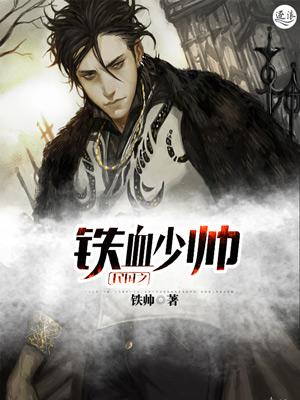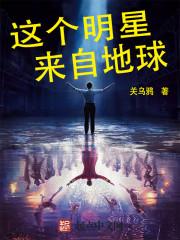奇书网>npcw > 年代文位面6(第1页)
年代文位面6(第1页)
莉莉在百汇大厦套房里研究政策文件的第三天,张主任带来的消息就像一盆冰水浇在了将熄未熄的炭火上,让她心头那点微弱的希望火苗“嗤”地一声熄灭了。
深秋的阳光透过纱质窗帘斑驳地洒在满桌文件上,那些印着“外汇结算”“中外合资”字样的文件还摊开着,钢笔尖在几个关键条款上洇出几团墨迹,像极了莉莉此刻郁结的心情。
套房的会客室里,张持安坐在法式绒面沙发上,脊背微微绷直,显得有些不自在。他粗糙的手指在人造革公文包的搭扣上摩挲了几下,才郑重其事地抽出一张带着车管所钢印的登记表。
“苏同志,有个情况。。。。。。”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在三轮车管理所那边查到了登记编号为个-056的车夫。”
莉莉注意到纸张边缘有些卷曲,显然被反复翻阅过。
张持安继续说道:“老马五十多了,在弘口踏了二十年三轮,我昨日专门去弄堂口堵了他。他说那天确实载过穿白色布拉吉的姑娘,但也就是普通乘客。在十六铺码头附近上的车,那姑娘全程都没怎么说话,到老北站付完车资就往人堆里去了。”
会客室里的落地钟发出沉闷的走秒声。张持安下意识去摸内袋,掏出半包皱巴巴的大前门,瞥见茶几上锃亮的镀金烟灰缸又讪讪地塞了回去。“至于车站那边。。。。。。”他喉结滚动了几下“每天进出的旅客少说五六万,检票员对乘客哪能有印象?这可比大海捞针还难。。。。。。”
莉莉望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指节无意识地在文件上轻叩。她早料到事情不会顺利,但没想到线索会断得如此干脆。
窗外的阳光忽然被云层遮住,房间里的阴影渐渐漫上来,将那些红头文件上的烫金标题也染成了暗红色。
沉默片刻后,莉莉忽然开口:“张主任对生产服务合作社怎么看?”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张持安手中的瓷杯晃了晃。他没想到莉莉会突然问起这个,愣了一下才开口:“生产服务合作社嘛,主要是为解决城镇返乡青年的待业问题。。。。。。”
要说他真正的看法,国营单位才是铁饭碗,政策刚刚松动,至于集体单位和个体户,连狗都嫌弃。
前段时间街道新办的修鞋合作社,三个小青年守着台老式补鞋机,每日里敲敲打打的声音隔着两条弄堂都听得见。
说白了,不过是街道为了应付上面的就业指标,随便给待业青年找个活干,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些人依旧是“盲流”。
这些回城的待业青年,总让他想起车间里没卡准尺寸的零件,既不入老工人的眼,也融不进新时代的机器。
可这些话断不能对华侨说。张持浮起干部特有的稳妥笑容:“这是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既解决就业又服务群众。。。。。。”
莉莉看他净说些场面话,便直接打断:“张主任每月接待多少华侨?”
张持安的后背沁出冷汗,白衬衫黏沙发靠背上。他忽然意识到这场谈话的主动权早已易主,几天前还是他端坐主位接受谢礼,此刻却像被推上供销社柜台的瑕疵品,等人验看斤两。
“侨联工作。。。。。。尚在起步阶段。”他说得含糊,耳根却烧得通红。上周路过虹桥宾馆,正撞见招商局的人簇拥着大侨商出来,那辆锃亮的皇冠轿车溅起的泥点子,此刻仿佛还沾在他裤脚上。
莉莉的目光扫过他粗糙的手指,想起昨天在张主任家看见的光景——五斗柜上的三五牌座钟缺了钟摆,用麻绳系着铁螺母权当配重,滴答声里都带着窘迫。
“政策开放后,归国建设的同胞只会越来越多。”她拿起文件下的一个准备好的牛皮纸袋推前半寸,“总该有个体面的接待处。”
张持安盯着纸袋上手写的英文花体字,忽然想起上月去外事办培训,洗手间里听见的闲话:“那个侨联的老张,英语还带崇明腔。。。。。。”
“我想投资侨联办个咖啡馆。”莉莉的指尖点在茶几桌面,“用合作社的名义,既能安置待业青年,又能给归国华侨提供交流场所。”
张持安的瞳孔倏地收缩。“咖啡馆。。。。。。”他无意识摩挲着袖口的磨边,眼前浮现出建国饭店的咖啡厅——去年陪外宾去过一次,银质雕花勺搅动咖啡的漩涡,空气里飘着资本主义的香甜。
莉莉忽然压低嗓音:“我研究过文件,侨联这样的单位是可以开办合作社的”她的睫毛在晨光中扑闪,像振翅欲飞的凤尾蝶,“本就是和华侨打交道的单位,有华侨捐赠是政策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