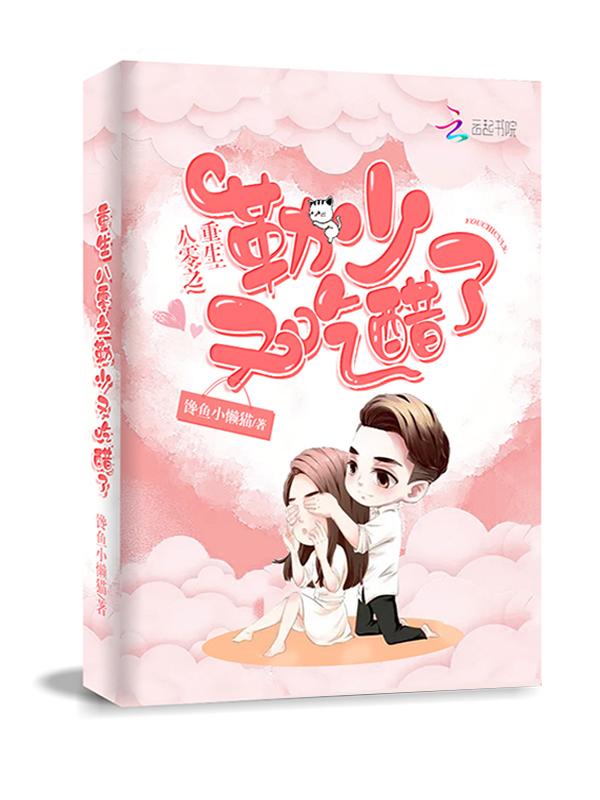奇书网>京城报娘晋江 > 第183章(第1页)
第183章(第1页)
“青嫩时可采来做菜,日常家里你也吃过,可是清甜可口?便是如今老干了,也可摘下晾干,用来装酒盛水,便是贫人不花钱的出行水具。”“剖开为二,又可舀水盛物,你看那图上的乞儿,腰间都少不了这件吃饭的家伙。”“就是内帷之中,也爱它多子多福的寓意,每常用作新婚之宴的吉祥物儿。”“此物生在穷壤,易于养活,世人都以为是贱种,或轻忽之,或怠慢之。它却不生愤懑之心,依旧奋力生长,尽心竭力,奉献所有,正如女子之德,亦当如是。”恒娘跟着鸣茶,在一边站定,听了这番话,顿觉大开眼界。葫芦这样东西,街边巷中常见,并无稀奇之处。偏这女子声音温和,娓娓道来,居然拿着它打比方,引申出一番贴合女德的大道理,实在神奇。鸣茶见了她神色,大为得意,悄悄与她耳语:“怎样?这位盛娘子,可是不凡?你以后少与那楹外斋的浪子交游吧,小心被她拐上歧途,到时候悔之晚矣。这位盛娘子,才是我辈楷模,女中尧舜——你知道尧舜是谁吧?”恒娘瞬间收回脸上敬佩的神色,冷冷看着鸣茶:“阿蒙是我好友,你如再有一句半句不尊重她的言语,莫怪我不知礼,从此与你绝交。”鸣茶没料到她说话这么不客气,大为尴尬,做声不得。那边盛娘子已被惊动,回头看到她二人,移步过来,到了身前,方用不高不低,合乎礼仪的声音,含笑柔声问道:“常家妹妹,这位,便是薛娘子吧?”恒娘按下心中的不爽,勉强与盛娘子点头:“正是。”来的路上,鸣茶已经与她热情介绍了,这位盛娘子是枢密副使、威武侯的女儿,父亲官至从三品,又有封侯,其母与如今的皇后又是一母同胞的姐妹,真正的贵女。若是以往,她见了这等贵女,心中定然惴惴不安,见礼自然也不敢草率,起码要矮身福礼,才算过得去。不过这段时间与阿蒙厮混惯了,熟了阿蒙那套不取繁文缛节的做派,再加上鸣茶一番话算是触了她的逆鳞,这会儿心里不高兴得很,压根儿不愿做小伏低。盛娘子果然是大度的人,并不与她理论礼节,反与鸣茶打趣:“常妹妹不请我们去内室坐坐么?还是觉得我们都是些不读书的浊人,不配登你家大儒的堂,入你这烈女的室?”鸣茶终于可以逃开与恒娘间的紧张气氛,长舒一口气,赶忙往里面让:“盛姐姐说这种话,敢是想让小妹无立足之地?两位快里边请,我让她们煮茶来,咱们好好说话。”——东宫。太子书房,有人正在发怒:“什么?廷议之上,由盛明萱代东宫出面?这是谁的主意?我不同意。”正是阿蒙的声音。道不同幡瓠院一溜四间房舍,鸣茶引她们去了西壁。入门处摆了张黑漆花腿四方桌子,三人围坐,空了门口一方,借着秋日天光,喝茶说话。“恒娘——我可以这样叫你么?”盛娘子笑道,“我闺名叫做明萱。”她身份最尊,坐了朝门的正位,恒娘在左,鸣茶在右。鸣茶正起身与她们张罗茶饮,听盛明萱对恒娘如此客气,忍不住看她一眼,心中赞叹:果然是大家风范,对着一个浣娘,也能如此有礼。恒娘却不肯叫她的名字,只是笑道:“盛娘子客气。鸣茶说,你想见我?”盛明萱便也不勉强,微微侧头,饱满匀润的银盘子脸上含着笑意,好似牡丹开花,雍容典雅。徐徐说道:“周婆言名满京城,听说其主编便是叫做薛恒娘,倒正好与薛娘子同名同姓。”“周婆言?”鸣茶眼睛一亮,“那日在太学,恒娘你不是就代表周婆言说话?”恒娘被鸣茶这一说,不好再抵赖,只能承认下来:“盛娘子猜得不错。我便是周婆言主编。”鸣茶欣喜,盛明萱却一派云淡风轻,显是早已知道:“今日冒昧求见,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要与薛主编倾谈。据我看来,周婆言为女子说话的立意是好的,不过行事的方法,报道的内容,却有失偏颇。”“哦,怎么说?”恒娘来了兴趣,放下手中茶杯,两手放在桌上,目光炯炯地看着她。难道这位盛娘子除了对葫芦之道颇有见识,还对报纸经营之道也有研究?盛明萱款款而言:“作为坊间唯一的女报,周婆言在报道的事例选择上,当秉承导人向善的宗旨,这一点,想必薛主编能够赞同?”“这个自然。”恒娘点点头。盛明萱见她认同,接着说道:“就拿周婆言近期报道的太学辩论来说,邓家娘子仗着自己有钱傍身,既不嫁人,也不招赘,竟想要一人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