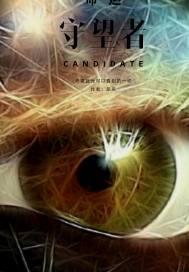奇书网>京城报娘晋江 > 第125章(第1页)
第125章(第1页)
仲简抬眼看看远方,高天之下,烟林漠漠,平野无际。想了想,答道:“学会骑马,你能走得更远。”“走得更远?”恒娘下意识重复一遍,也抬眼看过去,时值正午,三三俩俩的学子开始往公厨方向走去,随风飘来许多热闹人声。“你知道阿蒙与我说了什么?”恒娘狐疑地看他一眼。仲秀才这话说得,颇有些深意的样子。“不知。”仲简回答得十分干脆,“她说了什么?”恒娘想了想,把阿蒙问过她的问题,拿去问仲简:“你可知道,门下省是何人主持?御史中丞与何人投契?与何人交恶?计相刚刚出缺,如今何人声望最高,有望出任?谁赞成,谁反对?开封府陈恒与胡祭酒在政坛分属两派,你可知他们的争执与冲突?前任张祭酒又是因何离京?”亏她记性好,记得一字不差,连口气都差相仿佛。仲简了然。难怪恒娘一副倍受打击的样子。想到她本是一个浣娘,终日研究怎么浣洗衣物,突然被问到这些君国大事,那自然是两眼一抹黑,无所适从。居然有些想笑。这一丝微微笑意瞬间被恒娘发现,脸色一黑,怒道:“你笑什么?笑话我无知?”“你这些问题,我也很多不知道。”仲简坦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为什么要知道?你为什么要知道?”恒娘低了头,默默咀嚼这句话。“我为什么要知道?”“走什么样的路?”“夏云的事,不要报道。”“我不会对周婆言不利,信我!”许多人,说了许多话,嗡嗡地在她耳边回响。更远的时候,更多人的声音,也从记忆中泛起,那是被生活摧残过的声音,却响亮高昂,带着灼人的热烈:“我们都是周婆,这周婆,天下女子都可做得的。”秋日和煦,秋风肃杀,一冷一暖,激得肌肤一阵发紧。她眼望前方,举步便走,脚步越来越急,虽非奔跑,速度却远远超出往公厨小跑的人。到了后来,连伴她同行的仲简都微觉吃力。恒娘似乎并没有辨明方向,就这么一股脑儿闷头走下去,等她停下时,仲简看到,她原本苍白的脸色因疾行而泛红,额头挂着晶晶亮的汗珠,眼中反射秋日的光,明亮璀璨,耀得人眼花。半日以来,女人社长春殿是今上卧息的便殿,绣茵铺地,画帘低垂。九月的秋爽气候,殿里犹供着冰鉴,丝丝白烟被秋风一吹,袅袅消散。胖乎乎的手伸过去,取了半块西瓜。一个穿着青紫色圆领阑衫的高胖男子啃着瓜,口齿不清地说:“你继续说,捡些有意思的。朕听那些颂圣的话,听得耳朵出油。”“是。”仲简想了想,又说:“上舍如是斋刘得初、白蒙亨、刘观三人平日过从甚密,称兄道友,亲热无间。本月策试,三人都在一个考场。刘得初做完,卷中有犯先帝名讳。另两人见了,都不说。白蒙亨卷面也犯了讳,另两人也缄口不言。最后刘观写完,一样犯了讳,还是没人指出来。三人各自欢喜,都想着另两人必然见黜,自己便是本场的文魁。试卷发下来,才知道三人全都犯了忌讳。此事一时传为笑谈!”圆脸男子便是当今皇帝,笑得差点被西瓜籽呛着。内侍忙上前替他顺背。摇头道:“好,刘得初、白蒙亨、刘观,这三人名字朕记下了。若是他们将来有福气登第出仕,朕用人之时,可得多留个心眼。”仲简又道:“自官家下了谕旨,公厨的膳食颇有可观。小人去太学不到一月,到处听闻太学生歌颂圣德,不胜感激。”“安其卧起,丰其饮食,朕可以无愧于士人矣。”皇帝满意,放下啃了一半的西瓜,接过内侍递来的绢帕擦了手,又问道:“年前政事堂曾拟了旨意,命太学生课暇之时,前往武学校场练习骑射。如今太学生的骑射,练得如何了?”骑射?仲简紧了紧手指,小心回道:“回官家,小人观之,太学往武学者甚少。但有去的,都是一时俊彦。譬如上舍服膺斋有学子宗越,每旬必有日过校场。据说,有一日武学生下了战书,双方比试射箭。宗越十战皆胜。”皇帝笑了笑:“朕的武学生,居然敌不过一个书生?岂有此理。”皇帝听了宗越的名字,语气如常,似乎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仲简按捺下继续打探的心思,正想着再说些什么。忽然听到皇帝漫不经心地问道:“听说太学里有个浣娘,太子让她办了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