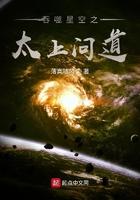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三侠之红拂女 > 第141章(第3页)
第141章(第3页)
“后来,没有哪里疼了吧?”
“……没有。”
“那……我有没有比上次进步一点点?”
“呸!”
“看你累坏了,想必我还是进步了的。”
“起开睡吧。”她娇声道,“明儿还赶路不赶路了?”
“不铺两个被窝了吧?抱着你睡得踏实。”
“抱着不行,硌得慌……”
高云桐大概是不大会违拗她的意思,于是稍过一会儿又是凤栖开始作:“两个人睡一个被窝有点冷了。风往肩膀里钻。”
他又是困得迷迷糊糊的:“那,我再铺一个被窝?”
“半夜三更的别折腾了。你的手到我肩膀那里把风挡住吧。”
他心知肚明地笑着,耐心地重新把她的肩膀揽在怀里。她的颈脖枕在他胳膊上,特感安心与踏实。
眼看他眼睛又闭上了,凤栖捏捏他的脸,问:“你那么多花样,是跟谁学的?”
他阖目笑道:“你猜……”
这怎么猜?男人的花样,又能是跟谁学?
凤栖心里又开始酸,欲待再问,可就是捏他的脸,他也像贪睡的猫一样,任她怎么折腾都岿然不动了。
第二天起身,凤栖有些慵慵的,揉着眼睛噘着嘴不说话,问就是“身上酸痛。”
高云桐虽不忍心,但还是看看日头说:“早上问了一圈,没有赁到肯去颍州的大车。今日还是得吃点辛苦骑马。你身上的伤刚刚上药……能行吗?“
凤栖自然是梗着脖子说:“怎么不行?”
但心里有点害怕,特别想到骑马时身体随着马匹起伏,马鞍子不断磨在皮肤上,还是挺折磨人的。
出门一看,马鞍上被他用厚厚的褥子垫着,凤栖伸手摸了摸软褥,回头又看了他一眼,他却在忙碌,把行李一件件搬到马背上放好,检查了辔头和肚带,检查了马蹄和马耳,扭头见凤栖还在怔怔地望过来,便拿着她的风帽过来,把她的头脸裹裹好,检查了斗篷上的蝴蝶结,才说:“如果半路觉得腿疼了就告诉我。”
“半路疼了,告诉你你能怎么办呢?”
他笑道:“与你下马一道步行咯。你看今天天气那么好,一路又是平川大路,晒晒太阳散散步,多么惬意呢!”
他开朗得浑不以一切苦难为意,凤栖被他冬阳般的笑意感染,不由也笑道:“行。我跟着你。”
不过垫子很软,腿上只有微微的一点疼,完全熬得住。
等一路到了下一个驿站,天色将将微暗,是颍州城附近的一个镇子。颍州是淮水边军事要地,所以周边递铺驿站都格外密集,地方也够大,来往朝廷邸报、臣民奏表、官私书信都很多。时不时响起递铺的“急脚递”鸣铃,驿站的铺兵就会牵好马匹准备接过急件往下一站递送。
这日便有好几个朱字的“红字牌”,高云桐给凤栖解释:“这漆字的木牌是递送皇帝诏书专用的,不那么急的用青字牌,急一些的用红字牌,再急的就是金字牌了,日夜传递,不能有丝毫耽误,接到令牌的官员如果不及时奉诏,就可算作十恶不赦里的‘大逆’或‘谋叛’,都是很严重的罪过了。”
凤栖问:“那这红字牌,当是爹爹发给吴王的咯?”
高云桐想了想:“你爹爹还是顾念兄弟情谊,不肯陷吴王于叛逆大罪里。”
红字牌所发圣谕,应该是劝服哥哥不要起兵造反,而要同仇敌忾的。
但他也忍不住说:“不知道吴王有没有同样的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