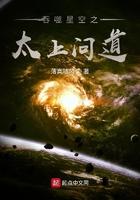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三侠之红拂女 > 第141章(第2页)
第141章(第2页)
磨破的伤最不宜触碰,但凤栖迁延了一会儿说:“那……试试吧。”
他靠近了一些,手努力伸长,虽然挺不容易,但那柔腻的丝裤被触碰到,感受到里面温温软软的肌肤,他喉头就发干了。伤在哪里好像半日也找不到了,睁眼便见她正屈肱侧卧枕上看着他,眸子里似笑非笑的。
他呼吸浊重,惺忪的神情完全被飞梭一般凌射过来的目光取代了。手也伸来揭开阻隔两个人的被子。
“咦咦咦,这是做什么?”凤栖明知故问。
“手不够长,够着吃力。”他笑道。
凤栖道:“想坏事就直说,别找这么拙劣的借口。”目光闪闪,含嗔带笑。
他越发笑起来:“不错,本来就该坦诚相待。不过还得问一句:你愿意么?”
“什么?”
“你要说想,我自当奉和,要是不想,自来也不敢侵犯。”
凤栖被他看穿心思,又无语应对,半日后在他胸膛捶一拳头:“你这个人好没意思!”
“如此,我明白了。”他笑嘻嘻的,厚着脸皮抱住她。
迟钝!还装君子!
凤栖心里狠狠地骂他。
于是在他亲过来的时候,咬了他嘴唇一口。
他顿时浑身肌肉偾张起来,伸腿压住了她两条腿,笑道:“好样儿的,今日不治服你是不行了。”
凤栖挣扎了两下无法动弹,可一点都不害怕,反而内心“怦怦”地激动起来,斜着眼眸看着他说:“你想干嘛?”
“奉泰山之命,行周公之礼。”
凤栖“噗嗤”一笑,见他俯低身子,影子如巨鹰一般,转而温柔又如柳绵,细碎的亲吻一点一点落在她的脸颊、眼睛、嘴唇、耳畔、脖颈……
她觉得有些痒兮兮,一边笑着一边躲让,恰见他面颊滑过落入她的腮边,侧脸便看见他弯弯的酒窝,于是忍不住吻了一下。
他笑意盎然,也再无顾忌,顺着她的肌肤游走着手指,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战栗而呼吸急促,温热而麻的触感一寸一寸激荡着胸腔和颅脑。
“上两次囫囵吞枣,真是怠慢了……”他说,“这次不能玩忽。”
凤栖脸滚烫,闭着眼睛只是想:其实就“那事儿”本身,好像也没多少大不了,温凌亲身“教学”时两个人陶醉的模样只怕也是装的……
不过他这次用心程度更甚于上次,好像也比上次游走得更加熟稔,她也愈发有些喘不上来气。
正想着,突然周身一沉,而不习惯的感觉袭来继上次之后,已然是半年多,居然还有点疼。
这还能忍,但腿上磨破的地方就不大能忍了,她从他双臂里挣开腿,扭了一下身子,又说了一声:“疼!”
他果然停下来,有些担忧地问:“哪儿疼?是我鲁莽了吗?”
“上药的地方疼,磨着蹭着,跟骑在马鞍子上似的。”她推了推他的腿他大概是娴于弓马,腿修长而肌肉很硬。
他挠挠头:“办法倒有,怕你不肯。”
凤栖怀疑地看着他。
他果然有办法。
更漏里的水连绵地轻响着,但时间对于帐中两个人已经没有了意义。
驿站简陋的棉帐,用靛蓝印着凤穿牡丹的花卉,那凤摇摇摆摆的,仿佛在牡丹间振翅翱翔,忽而摇摆得剧烈,似乎就要飞上九天云霄,然而忽而又缓和下来,帐子缝里溢出浅浅的喘息和浅浅的幽香那似瓷香炉里燃到最后一刻的麝香一般,浅淡、奇异而满是诱惑的芬芳。
帐子上的凤凰终于栖落下来,帐子里传出喁喁的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