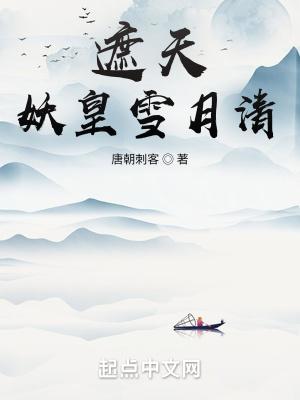奇书网>npcw > 年代文位面3(第1页)
年代文位面3(第1页)
不久,服务生端着鎏银托盘稳步走来。
第一道蟹粉小笼包呈在青花冰裂纹浅碟里。半透明的面皮吹弹可破,能望见内里琥珀色的汤汁轻漾,每只顶上缀着粒鲜红蟹籽。莉莉用银匙托着轻咬破口,混着姜丝的蟹黄鲜气裹着滚烫汁水涌出,与黑醋的酸冽在舌尖缠成一道微妙的弧线。
接下来是一道古法烟熏银鳕鱼。松木香气氤氲腾起,鱼肉表层焦糖脆壳裂开的刹那,露出雪瓣似的嫩肉,淋着调制的琥珀色酱汁,底下垫着的荠菜豆腐羹泛起翡翠般的光泽。
压轴的腌笃鲜端来时,黑陶砂锅还咕嘟作响。侍者用铜钩挑起锅盖,白雾轰然漫起。汤色是种温润的玉白,金黄油星在笋尖打转,咸蹄髈与五花肉卧在春笋林间,砂锅底的火踵骨已熬出蜂巢状髓孔。莉莉舀起半勺轻吮,火腿陈香混着春天气息在唇齿间炸开。
回客房路上,莉莉数着走廊壁灯投下的光斑,吃腻系统套餐的滋味,此刻舌尖残留的鲜甜竟让她眼眶发热。
一夜无梦。
晨雾尚未散尽的早上,莉莉已经站在侨联小院斑驳的砖墙前。十月的晨风裹挟着凉意,她下意识拢了拢米色风衣的领口。
褪色的黑板报上,“团结侨胞”四个粉笔字被夜露洇得模糊不清,水痕顺着斑驳的墙面蜿蜒而下。
接待窗口内,老干事的蓝布袖套洗得发白,袖口处还留着几点墨渍。他正用放大镜逐行检视文件,金属框偶尔磕在玻璃台面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
“苏小姐昨日才到上海,怎么就。。。”老干事突然抬眼,镜片后的目光像秤砣般沉甸甸地压过来,“急着返美?”
莉莉的指尖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两下。晨光透过梧桐叶的间隙,在她手背上投下摇曳的光斑。“原是为着叔父遗愿回国投资,”她的声音比晨雾还要轻,“现在美国那边的信托出了些状况,必须亲自回去处理。”
说着,她将准备好的文件推过窗台,存款证明上那一长串黑色数字在晨光中格外刺目。
老干事枯枝似的手指突然痉挛起来,“个十百千。。。两亿?美元?!”
钢笔从他指间滑落,在桌面上咕噜噜转了个圈,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但老人已经顾不上了,他猛地站起身,膝盖撞到抽屉发出闷响。
里间立刻传来窸窣的响动,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深蓝色的中山装衣角扫过门帘时,带起一阵陈旧的樟脑丸气味,混合着铁皮柜里的文件霉味,在接待室里弥漫开来。
“苏小姐你好,免贵姓张。”张主任伸手相握,力道拿捏得恰到好处,掌心带着常年批阅文件留下的薄茧。他的目光在莉莉身上短暂停留,又瞥向窗外梧桐树上新挂的红色招商引资横幅,嘴角微微上扬,“您这样规模的海外投资,正是国家现在最需要的。”
莉莉适时地垂下眼帘,浓密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当话题转向叔父在旧金山的发家史时,她的嗓音微微发颤,尾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他老人家临走前。。。。。。还在念叨着要落叶归根。。。。。。”这句话说到最后几乎变成了气音,仿佛下一秒就要控制不住情绪。
这套说辞,她昨夜已经反复演练过二十七遍。
在落地镜前,她对着自己的表情精雕细琢。眉心的蹙起要恰到好处,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眼角的湿润要若隐若现,不能真的流泪;嘴唇的颤抖要控制在第三秒开始,持续不超过两秒。
莉莉甚至借了酒店的座机,假装打了一通跨国电话,确保走廊外等候的酒店经理能听见她焦急的英文对话。系统提供的资料足够详尽,但细节才是关键——一个归国华侨的微表情、语气停顿、甚至是呼吸节奏,都必须天衣无缝。
张主任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略长于正常社交礼仪,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苏小姐的国语倒是标准。”他突然开口,指节在实木扶手上轻轻叩击,“上月我接待过一位华侨青年,把‘实事求是’说成了‘四四酒席’。”
这句话看似闲聊,实则暗藏锋芒。
莉莉心头一紧,但面上丝毫不显。她微微抿唇,露出一个略带苦涩的微笑:“家族一直很重视传统教育,从小就要我们熟读四书五经。如果不是。。。。。。”她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袋的皮质表面,“如果不是长辈们都不在了,如今也轮不到我这个小辈,带着这些资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