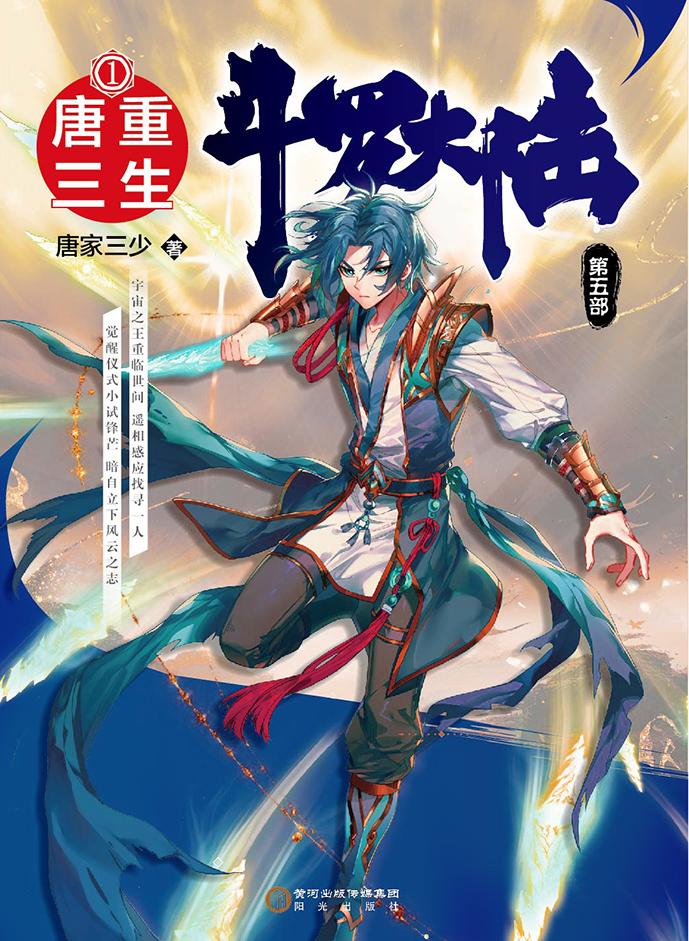奇书网>任凭君凭栏我栖春山 > 第183章(第1页)
第183章(第1页)
当她失明,看不清东西,很好欺负是吗?
沈春芜越是想,越是难过。
日思夜想的人,一直以为远在天边,原来就近在眼前。
她不知道他是他,他分明知道,却不告诉她。
这天底下,怎的会如此可恶之人!
沈春芜这一咬,用了蛮劲。
空气之中,逐渐弥散着一股子血腥气息。
她听到身边的男人传了一阵低闷的轻哼。
沈春芜松开了嘴,抚着他的肩肘,别扭地问了一声:“疼吗?”
“一点都不疼,”盛轼反而揉了揉她的嘴唇,关切道:“你牙齿疼吗?不疼的话,可以咬另外一边。”
说着,把另一个肩膊腾了出来,送到她嘴前。
沈春芜:“……”
她泄恨泄够了,自然不可能再咬他。
彼此都冷静下来后,沈春芜忽然变得有些腼腆起来,一直垂着脑袋,两只手藏在毛氅里,小幅度地揪着绒毛,觉察到盛轼的目光一直落在她身上,目光温沉而柔软,裹藏着执着的烈火。
沈春芜有满腹的疑问,张了张口,一时之间却不知该如何问起。
此际,只感受到盛轼一边替她绾发,一边好整以暇地问:“怎的现在不说话了,嗯?”
“我记得,当初为你撑伞的几年,你小嘴挺能叭叭。”
沈春芜:???
她本来想要反驳几句,但听到了“撑伞”二字,她意识到了什么,眸瞳在昏暝的光影之中缓缓瞠住,大脑轰的一声,全乱了,不可置信地道:“当初在檐下,给我撑伞的人,是你?”
盛轼微抿下唇,嘴角漾起浅浅弧度,眼睑耷拉望着她:“那个时候,我其实在等夫子传信,但突然见你钻到伞下,你还吩咐我,送你回家。”
他如今肆无忌惮地清算起旧账,沈春芜颇觉羞窘,恨不得寻个洞,把自己给埋进去。
沈春芜嗓音变得轻如蚊蚋,两只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戳了戳:“我以为你是来接我回家的侍卫,我就是忘带伞了……”
“一两次忘记也就罢了,连续三年都能忘?”
盛轼故意拖着腔调,闷声低笑。
沈春芜心口上仿佛有小蚂蚁在慢条斯理地爬,所及之处,皆是撩蹭起漫天的麻意。
她被逼急了,忍不住道:“那你为何不主动声明,这样我也不会走入你的伞下。”
顿了顿,她反问起来:“第一次许是无次,第二次为何还要送?”
“第二次为何还送,此中缘由,你不知道?”
男人这一声反问,径直酥入了他的骨头里。
七年前毛毛细雨里,他故意撑伞,送她回山居,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