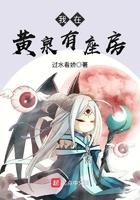奇书网>大宋神探志TXT笔趣阁 > 第468章(第2页)
第468章(第2页)
狄进正色道:「在下年少,本不敢着书育人,然慕于先祖狄梁公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再见地方官员,多轻实证重刑罚,便试着此刑案之作,望天下间的冤假错案能越来越少!」
李允则对此是真不清楚,闻言也有些半信半疑,谨慎地让年轻识字的仆从念了起来:「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所以通着今佐理据者,谨之至也……」
当序章读完,明了此书的核心思想「人命大如天」,李允则深吸一口气,终于没了疑虑。
一位着书立言的三元魁首,绝非可有可无的国朝小官,确实可以破格当上馆伴使!
如此一来,不仅解决了朝堂如今的任职难题,还能在两国接待中,顺理成章地调查使节之子无故身亡的要案!
而想清楚一切关隘后,面对这位未雨绸缪,能将各方利益都考量进来的年轻三元,李允则定定地打量了一番,最终忍不住再度发出这一声感叹:「真是后生可畏啊!」
太后特赐五品服
夜深人静。
机宜司中。
烛火仍然燃着。
提举刘知谦坐在桌案前,看着一份份尸格,眉头紧锁,拧成一个川字。
死者不是正常人,而是一个经过七天严刑拷问,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犯人,所以仵作验尸后,给出的尸格都是长篇大论,但核心有一点,基本都认为这个人是被打死的。
刘知谦并不认可,觉得犯人暴毙,肯定有另外的死因。
这一局的关键,就是大使之子,要死在机宜司的牢房中。
如果人不死,哪怕受了刑,也能说成一场误会,毕竟对方确实是偷入京师的,吃点苦头,还能怎的?
但人一死,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犯人之死不可能是审讯的意外,要么使用了某种仵作检查不出来的手段,要么……机宜司中早有「金刚会」安插的内女干?
刘知谦揉了揉眉心,将这个念头压下,他很清楚,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候,如果再怀疑身边的人,那就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
而且有内女干安插的可能性确实也不大,毕竟机宜司的创立是曹相公临时提出的,然后强势组建,整个过程十分迅速,「金刚会」能通过使节团设下这个陷阱,就已经很了不得,如果再安插内女干,那就真的无所不能了……
刘知谦不再胡思乱想,回到眼前的关键问题上。
如果能拿出证据,犯人萧氏的死亡,不是因为机宜司的刑罚,而是别有目的的手段,那么就重新占住了理,在外交上至关重要。
所以刘知谦将仵作的报告再度看了一遍,突然道:「这里只有七份尸格,我怎么记得从各处调来的,是八名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