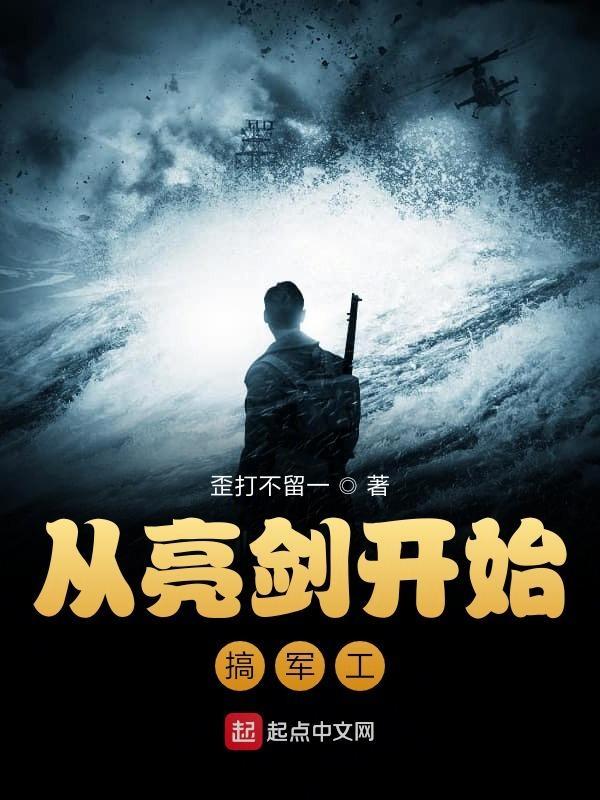奇书网>美人谋演员表 > 第383章(第2页)
第383章(第2页)
“立一个襁褓中的婴孩为储君,这真的是陛下的意思吗?”裴长之问出了心中埋藏已久的困惑,“自涪陵回京,我等众臣便再未入见于陛下,一切政令,皆从妇人之口出,然而早在大楚建立之初,便有内廷不得涉政之祖制。”
“立十九皇子为太子究竟是谁的意思,陛下为何不见众臣,中宫百般阻扰,是何居心,而在立下年幼的太子后,陛下又为何突然驾崩。”
张伯阳作为武将,自然争论不过身为老臣的裴长之,“尚书令…”
“裴某只想要一个解释!”裴长之呵道,“以及改立十三皇子李宗,还政于新君。”
裴长之与一众士大夫早已看出平阳公主的野心,只是因为武安侯在京,且中领军韩修态度不明,才有所隐忍。
然而平阳公主却在之后不顾劝阻,执意立李兴为太子,女主主政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他们便也越来越恐慌与不安。
“公主呢?”张伯阳问道身侧的宦官。
“在承明殿。”宦官回道。
平阳公主带着张贵妃母子等候在楚宫正中间的大殿,承明殿内。
两军博弈,胜负难料,但,平阳公主比这些文臣要有更多的筹码——边军。
外面冲杀声不断,经历过一次兵变的张贵妃,心中充满了不安,李兴诞生于腥风血雨之中,如今又因储君之事,闹得满城风雨。
“兴儿还太小,公主立他为帝,宗室与群臣自然不会答应,楚国已经遭受了太多的动荡。”张氏看着平阳公主,她虽是妇人,却也明白平阳公主拥立李兴所面临的阻碍。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平阳公主坐在殿阶之上,擦拭着手中的利剑,“要么成功,要么成仁。”
第327章承明殿之变
张氏抱着自己的儿子,眼里充满了担忧,因为李兴的年幼。
跪坐在殿柱白绫下的秘书郎赵砚书放下手中的笔,“贵妃娘子。”
“太子殿下乃是昭告天地丶宗祖行过册封礼的储君,国之正统,先帝大行,储君继承大统,乃是礼制,尚书令裴长之作为文官之首,中领军韩修作为禁军统领,却在先帝尸骨未寒之际引兵入宫,行谋逆之事。”
“这种时候,娘子应该要有底气抗争才是,因为宗法与礼教,不会站在佞臣那边。”
“他们的阴谋,也不会得逞。”说这句话时,赵砚书将目光转向了平阳公主。
因为他在平阳公主的眼里,没有看到一丝的慌张与惊恐。
对于裴长之与韩修的造反,平阳公主似乎早有预料,她在等这一天。
涪陵之乱,天子病重,已非秘事,故而天子驾崩,也并非突然,但平阳公主却选择了隐瞒,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激化矛盾。
而平阳公主所做的一些举措,也像是在试探,试探这些士大夫们的底线与容忍,随着矛盾越来越深,他们再也无法隐忍,最终爆发斗争,平阳公主便可藉此机会,将朝中的阻碍,连根拔起。
在赵砚书的一番言语中,怯懦的张氏忽然清醒,皇帝没有嫡子,诸皇子拥有同样的竞争资格,而在她的儿子被确立为太子后,其他人便失去了资格。
群臣的做法,无异于造反,造新君的反,“我明白了。”
“告诉裴长之与韩修,还有他们手底下的禁军,新君已于承明殿继承大统,私自带兵入宫,视为谋逆,放下武器归顺者,既往不咎,否则…”平阳公主看向张伯阳派来的传信士卒,“格杀勿论!”
“喏。”
平阳公主的话,并没有让裴长之与韩修退缩,他们太清楚平阳公主的手段了,从他们决定发动政变开始,就已经想到失败后的结果。
不出所料,禁军们在宫中展开交锋,韩修的中领军与张伯阳的中护军在楚宫正大殿前厮杀了起来。
张伯阳刚入中护军府没有多久,对于宫中也没有韩修那般熟悉。
于是在僵持了两个时辰后,张伯阳的兵马逐渐不敌,被迫退往承明殿。
盛夏的黄昏,阳光依然格外刺眼,寒冷的兵器上沾满了鲜血,晚霞照在了血泊中,血色与霞光交融在了一起。
今日的楚京城,百姓们闭门不出,中立的官员包括那些受平阳公主扶持的官吏,也都躲在官邸内不敢出来。
他们在等待结果,是继续依附平阳公主,还是接受拥立新君。
至于立场坚定者,如今都在宫中对峙与厮杀。
韩修执掌中央禁军多年,对于这场内争,势在必得。
按照裴长之的计划,在他们夺权成功之后,便可以利用新君号令天下,调西南边军与州郡常备军加上禁军与萧怀玉的边军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