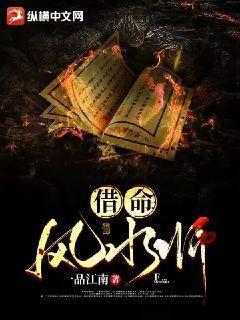奇书网>蝴蝶坠落笔趣阁免费阅读最新章节更新内容 > 第106章(第2页)
第106章(第2页)
南嘉额头靠着,很低地呜了声,没有骂他也不挣扎,自?知?无果,堪堪将人附着维持平衡。
没有关严的窗户游来夜风,不冷,可蝴蝶骨缩着,人也下意识往里收,真的撑不住了开始哽咽,指尖攥他衣角,“陈祉。”
他才见她?哭了,眼?角挂着晶莹,泛杏红,鼻头也弥漫绯色,他便停顿,也退出去一些,拂过?她?的泪,“哭什么。”
本来不觉得是什么伤心?事,眼?泪是被感官刺激出来的,不见得多难过?,可他这话一来,她?又落了一泪,额头抵心?口,很小地坦白,“难受。”
“哪里难受。”
她?呜得更大声,“你怎么那么讨厌。”
还要问,更讨厌了。
这一声质问,卸了人所有盔甲似的,变得手无寸铁,心?跟着软塌,可人没软,反倒愈演愈烈,他不出去,淡淡撇了句,“下次轻点。”
南嘉眼?泪敛住,怨念,“为什么下次,这次不行吗。”
“不行。”
“拿,你拿回去一点吧,进得太多了。”
连说话的声音都软弱哀怜。
他应该是听见了,没有任何怜悯停歇的意思,浅浅低声应了声,可没有作改变,不过?是在边c边哄顺带帮忙抹眼?泪。
常言道,这时候的话是最不可信的,他哄得也没什么诚意,叫BB,叫宝贝,就是不停。
其实该来的迟早要来,总不可能一直三分之一,留着三分之二在外面候着,不过?是挑了个他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所以进得没有顾虑。
知?道没用,知?道结果,南嘉就不再求他,死死咬唇受到最后?,乏得走不了,陈祉照例照顾小动物似的,清洗再带回绒被里。
“周嘉礼。”他半撑着,臂膀捞人,半带威胁商量,“以后?能不能别骗我。”
她?别过?脸,“不能。”
声哽着,听着像气话。
他就问:“为什么?”
“你讨厌。”
每次她?说他讨厌,他总会安静那么一会儿。
这次安静得有点久了,死水一般,情绪坠落海底。
陈家太子爷自?小呼风唤雨,受人追捧,偶然?遭人讨厌,说两句诋毁,蚍蜉撼树,他嗤之以鼻,压根不会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