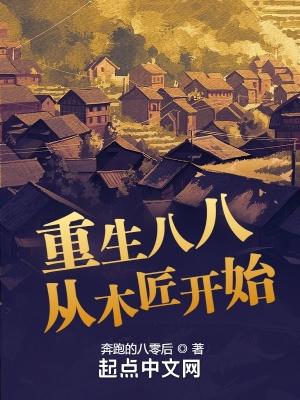奇书网>嫁给黑莲花霸总后我后悔了格格党 > 第88章(第1页)
第88章(第1页)
那是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全是她的照片。在笑的,在发呆的,趴在窗边闭着眼的。灯忽然关了。静谧的空间只有铁链贴着地面乱晃的声音。像蛇。完全黑暗的空间,林知安感觉身上一凉,细细密密的风从失去遮挡的四周灌进来。但是她某些地方却是暖的。有什么温柔熨帖。木板嘎吱嘎吱作响,铁链像一叶在疾风骤浪中翻滚的小舟,倏而撞上床头的柱子,哒哒哒乱摇。不多时,手腕上的小银镯被汗雾湿了,交缠在一起的手时不时缩紧,就像花瓣被人用力推开,露水从里面翻折滚落。林知安心口堵得慌,闷闷钝痛,她不明白,为什么苏佋会变成这个样子,变得这么可怕阴森。她鼻子一酸,放声大哭。“安安?”有人在摸她的脸,是温热的。床头灯亮了。林知安眼泪止不住的流,一粒一粒委委屈屈滚进枕头里。她迷茫地抬眼,苏佋正温柔地给她擦眼泪,衣服整整齐齐穿着,他们手上也没有铁链。“做噩梦了?”苏佋把她从被窝里抱出来,像哄小孩子一样拍拍她的背。苏佋睡衣很薄,温热的体温像一股暖流灌进林知安血液里,心头那股寒意驱散了一些,瘪瘪嘴抓住他手臂,闷头不吭声。之所以会做这个梦,要怪就怪书房里那个袋子。林知安没在哭了,只不过心脏还是砰砰直跳。梦境里发生的事情太过真实,她甚至能感觉到温热浓重的液体填满自己时的颤栗感。思及此,她又有些羞耻,松开手离苏佋远了一点。“安安梦到了什么?哭得这么委屈。”苏佋薄薄的眼皮半掀,顺着她头发,仿佛随口一问。苏佋在这个梦里是大反派的属性,林知安不好意思说,嗫喏道:“梦……梦到被坏人关起来了。”“嗯?怎么关的?”苏佋专注地把玩着她的头发,嗓音懒洋洋。“就是……在一个很黑的地方,里面什么都没有。”床头灯暖融融地照着,林知安放松很多,说话也顺畅起来。“所以安安是被关进了小黑屋。”苏佋嘴角勾起微不可察的弧度,“他对你做了什么?”林知安咬了下唇,低头小声说:“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那安安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嗯?”苏佋原本勾着她发梢的手指一移,微凉的指骨弓起来,在她眼尾轻轻摩挲。“我忘了。”林知安眨了眨眼,脸颊吹起似的一鼓一鼓,视线挪向地板。逃避他。小骗子。苏佋轻笑了声。半晌,林知安又转过头,“苏佋,书房那袋东西什么时候还给你朋友呀?”“怎么了?安安很在意吗?”苏佋表情十分平静,长睫一眨,眼眸清澈又无害。林知安第一眼就对那袋东西感觉不好,再加上这个莫名其妙的梦,现在还心有余悸,很好心地提醒,“他给女朋友买这些东西看起来就不像好人,你不要和他走太近。”苏佋笑了笑,“这种东西在床上用可以增加情趣,又不是买给我们,安安担心什么。”林知安摸了摸手腕,梦里苏佋用力撞向她时不时扯到链条的瞬间,银镯像是嵌进她的皮肤里,很冰很痛。她皱了皱眉,“反正不太好。”苏佋慢悠悠扫了她一眼。她似乎完全没感觉在床上谈论情趣用品是一件多暧昧的事,温柔道:“嗯,我知道安安的意思了。”说了这么久的话,林知安已经彻底从噩梦阴影中走出,娇气地打了个哈欠,眼睛雾蒙蒙的。转头对苏佋说:“我困了,我要继续睡了。”苏佋“嗯”了声,关灯,在黑暗中注视着身侧的小姑娘,眼眸清亮,半晌,唇角勾了勾。仿佛刚做完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然而过了几分钟,不知想到了什么,他表情又变得阴沉起来。做那种事她应该感到快乐才对,为什么她会哭呢?她不喜欢他碰她吗?苏佋看向床头柜的催眠专用香眯了眯眼。苏佋和霍青荣吵了一架后没有再回老宅的意思。林知安不用交际乐得轻松,在霍蕾生日当天给她发了一段祝福。霍蕾有点可惜:本来还想给你介绍几个喜欢画的朋友,现在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了。林知安弯了弯眼:没事的。霍蕾很爱拍照,几分钟后两个人的对话框就只剩下照片了。林知安一张一张慢慢看,看到一个漂亮优雅的知性女人,回复道:你们看起来感情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