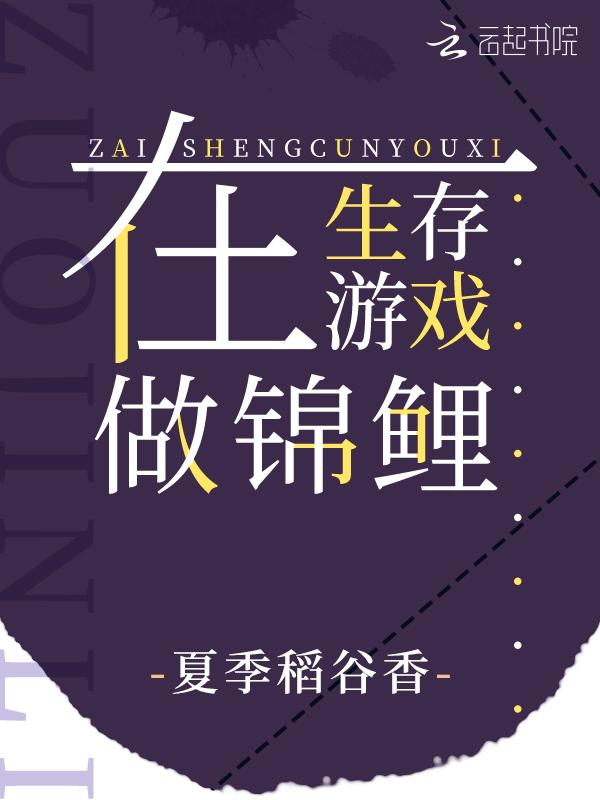奇书网>行医在三国by > 第270章(第1页)
第270章(第1页)
李隐舟皱眉:“谁?”凌统微拧起眉,眼神顿时冷在风中。“张辽。”……和凌统攀谈片刻,李隐舟算是明白了眼下孙权不安的另一个原因。魏王已不是战无不胜的神,可他依然是那个深谙人心的曹操,专程调遣了大败孙权的张辽屯兵居巢策应濡须,用心可谓昭然若揭。还偏能奏效。有这样一个气吞山河的悍将把持后路,曹操此行可谓肆无忌惮。而对于吴军而言,这无异于噩梦再临。胜,或许会被张辽逆风翻盘,再历经一次逍遥津血战;败,尽管不至于倾家荡产,但也将不得不把数代将军耗尽心力打来的长江北岸拱手送人。输赢的结果都令人惴惴不安,种种利害矛盾交错,吴军指挥部不吵架才奇怪了。战未开,人和已失。鲁肃不立即给出意见,一面为的是保全孙权主公的体面,不事事置喙与他冲突,另一面也是为了避开争论,再另寻别的办法。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曹操虽然巧妙地利用了人和,却倒霉地输掉了天时地利。陆绩根据星象预言出的这场寒疫,始于曹军。所以,胜负还不一定。甚至于能不能开打都是个问题。两人一路走着。一点白芒划破苍翠如雾的天色,轻落在温凉的脖颈上,倏忽间消弭不见。路上的行人皆有些惊讶地仰起了头——早春三月,竟然下起了雪。茫茫的雪从空中钻出,只顷刻便覆了一周的霜白,将那初生的万物重新凝如寒冬。凌统搓了搓有些冻结的手,忽看了李隐舟一眼,解开批甲丢过去:“这里比不得吴郡,天气怪得很,你且当心。”李隐舟接过那沉甸甸的批甲,却动也不动,只停下脚步凝住视线:“你方才说,曹操父子亲率大军,可知道跟着魏王的是哪一位?”是精明强干且有司马懿为智囊的曹丕,还是文采飞扬亦有杨修支持的曹植?凌统回头,目光有些微妙:“那两位,都来了。”果然。曹操大限将至,北魏世子之争亦被提到了明面上讨论,曹丕有嫡长子的尊贵,曹植则因文采风流得曹操欢心。两派明里暗里斗得轰轰烈烈,这场极具优势的战役自然也就成了二人展示本领与作风的一场试炼。李隐舟忽明白——这对于势在必得的魏而言,濡须一战实际上也是一场苦斗。而战场,就在他们的军营之中。“李先生……”凌统长眸一狭,有些欲言又止地望着止步不前的李隐舟,用眼神无声息地问——你该不会打算在世子之争做文章吧?曹营可不是你李隐舟的后院!何况赤壁之战他的一番筹谋已经助其大败,只怕一露头就会被愤怒的魏军剁得渣都不剩了,恐怕再无有诡言巧计的机会。李隐舟目光回拢,便从凌统复杂的表情中读出他的所想。诚然,曹操绝不可能被一个人戏耍两次。而时疫干系无数无辜,一举一动皆要慎而又慎。他拂了拂披甲上薄薄的一层雪,淡问他:“主公给了你六百私军吧?”凌统下意识警惕地拧了拧枪。这是把主意打他头上了?李隐舟却是笑一笑,极随和道:“放心,不动你一刀一戈,不损你一马一兵,只问你借不借?”凌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借岂不晓得他小气得很,半点不够仗义?何况李隐舟还冒死救了他的命,换了他的眼。李隐舟见他龇牙磨齿地片刻不语,无奈地叹一口气:“你不肯也无妨,我只能找甘将……”噌!银亮的枪尖挑着一枚令牌,在眼前微微晃动。凌统额角抽动着:“你要是……”“多谢。”李隐舟打断他的叮嘱,将那令牌摘下纳入囊中,拔脚继续往前走着。擦过年轻的偏将军肩侧,顺便抬手拍了一拍。“走了。”凌统:“……”他大约知道为何曹刘都咬牙切齿想宰了这人了。三月十五,夜静月满。无边细雪茫茫铺在天地之中。偶有朔风卷地吹起薄积的雪尘,颇有节律地轻声扑打在半掩的窗格上,将夜的深寒顺着湿润的窗格浸入灯火通明的房中。濡须的太守府已设为指挥大帐,此刻孙权正亲在此地、负手长立于窗前明光之中。月色擦过深挺的眉峰落下一层层淡淡的影,他眼底那按捺不住的戾气分明地滚涌在满目阴霾之下。身旁的陈盛只觉一种山雨欲来、雷霆如鸣的压抑沉沉布在肃杀的空气中,一抬眸却只见主公微搭下双目,只眉尖一点轻微抽动了下,竟是怒极而笑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