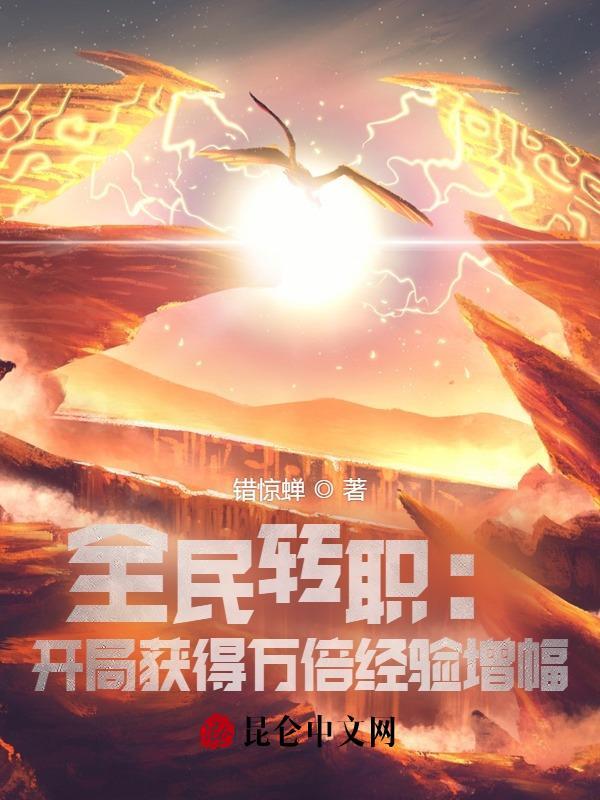奇书网>双生夫郎互换人生后笔趣阁最新 > 第216章(第1页)
第216章(第1页)
陆杨也不知该不该要,他觉着乌平之好过头了。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他们家这个样子,没什么值得惦记的。还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啊?
他说:“这多不好意思?说是我们请你吃饭,上门一趟,连吃带拿的,我都脸红。”
乌平之给他俩倒酒,还配了茶水,两种水都满上,随他们喝哪种。
“你不知道,我跟谢岩是老交情了,认识得有十年了,他一直这德行,我都是热脸贴冷屁股。你还别说,人嘛,就好这一口,上赶着的不要。这叫缘分。”
陆杨来了兴趣:“那你俩怎么聊到一块儿的?”
谢岩抢答:“他喜欢读书。”
乌平之都笑了:“弟夫,我们聊我们的。”
谢岩不高兴:“你跟我夫郎聊什么?”
乌平之拿捏他:“你不是说下次见面就要跟你夫郎聊吗?是这回吧?”
谢岩认了。
陆杨举杯喝茶,虚敬乌平之:“我们聊。”
他俩是聪明人,前情往事不提。
什么这样好的关系,以前却不帮谢岩脱离苦海,都是虚的。这话陆杨不可能说。
以他的经历来讲,罗家兄弟待他再好,也没法子把他从陈老爹手里捞出来。还得陈老爹自己放人。
陆杨嫁出来,才海阔天空了。
谢岩也一样,旁人千帮万帮,也要他自己肯立起来。
乌平之说:“进县学之前,我们都是在私塾读书,那会儿谢岩他爹还是教书先生,打我的板子比我爹骂我的话都多。我爹急得上火,跑私塾都跑了不知多少遍,见了人,又屁话不敢说,只骂我。
“我一天天的,不是挨骂就是挨打,就看谢岩不顺眼。他学问好,爱看书,还有个爹当夫子,私塾的小书生都不跟他玩,我去找他,说是捉弄他一下,但你瞧他这样,没劲。
“后来我发现他什么文章都看,那么些个稀烂玩意儿都捡回去当个宝,他还装订起来了。我那时小,没别的想法,就觉着我可以多写点烂文章,膈应他,把他带歪。没想到他是个傻的,他看我写文章好勤快,但写得好烂,心疼我读书辛苦,常常来找我,教我怎么写。”
这些东西陆杨爱听,谢岩自己说起来没劲,听别人说才有趣。
陆杨给他满上:“再说说。”
再往后也没什么有趣的东西了,乌平之说:“你家夫君这性子,一辈子能有几件趣事?这还是在我身上找的乐子。”
乌平之把酒喝了,又道:“那讲个丢人的吧。他刚开始来教我,我别扭,不听。我想装一装,我凭什么听他的?我不听,我写得烂,那就是我不想学。等我想学的时候,努力了一把,谢岩说我那文章跟从前写得一样烂。我是想着装傻的,结果是真傻。”
陆杨笑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