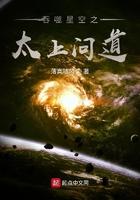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经略红楼全文阅读洪淏 > 63借刀杀人(第2页)
63借刀杀人(第2页)
洪淏忽问:“先生与缮国公石家可有交情?”
贾化一怔:“他们家不比贵太岳府上,石家早前是锦衣内卫,如今还是从武之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便有心结交,怕也没有许多话说。”
“先生果然高见!”洪淏巡视左右,压低声音说道,“我有一件为难的事儿,不巧师父出京,寻不见有阅历的长辈请教,先生在此,可能为我参酌一二?”
贾化笑道:“你我之间,何须见外?”
洪淏缓缓说道:“我有一位好友,很看不惯石家做派,他的本心,必要晓以颜色才好,只碍着身份,不便向他发作,我有心替他分忧,想了几日,没有正经主意,先生可有法子没有?”
贾化心中一惊,面上倒未显露,因向洪淏笑道:“若论旁事,我未必能尽绵力,如是这样的事儿,你找我,比林大人还要强一些?”
洪淏喜道:“先生有法子?”
贾化连连点头:“我如今协管欠银追缴事宜,缮国公石家就有九十多万积欠,你晓得,老一辈的体面,早前不好催逼过甚,他们家,几个月才凑了三四万两,正该立个筏子出来。”
甄应嘉同贾化清缴欠银,头一家便拿南安王府开刀,南安王府获罪不久,眼下家计尚可,倒把欠银还了半数有余,贾化见好就收,又去催缴闲散宗亲、没落勋贵,倒不曾触动八公这样的显爵人家。
洪淏拊掌大笑:“这正是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先生随机应时,必可官运亨通、前途无量。”
贾化大喜:“多承晋嘉美言,雨村感激不尽。”
洪淏刻意叮嘱:“既是师出有名,我的浅见,不露痕迹最好,我那好友,倘若行事偏颇,少不得会有物议。”
贾化满口应承:“这是自然,你放心,我是秉公办事的,与旁人并不相干。”
缮国公府虽有欠银,当下出孝未久,并不曾料到,贾化先就寻到自家身上,缮国公府门长、现袭一等将军石光珠颇为不不满,当面向他问罪:“你只问我们家要呢,还是别家都要归还?”
“自然都在归还之列。”贾化将半年间还银数目说了一遍,“到现下,连南安王府也还了一半,以此为例,府上若不宽裕,将军先还五十万两即可。”
石光珠变了脸色:“宁荣贾家、牛家、柳家可都还了?”
贾化淡淡说道:“不瞒将军,下官原也为难,不知先去谁家讨欠,索性抓阄定次序,头一个拈着了将军府上,下官又觉好笑,都为王事,八家公府待陛下忠心皆是一般,何必多此一举?”
石光珠气个倒噎:“你拿圣人压我?”
“不敢。”贾化拱一拱手,“下官奉旨办差,将军自然不会为难下官。”
石光珠伸着手,颤巍巍问道:“我待不还,你要如何?”
“将军若执意抗旨、违逆君父,下官舍了这条性命,今日便与将军不死不休。”一言既出,贾化摘了乌纱,一头便向门前石狮撞去。
石光珠吃了一惊,又见两厢差役去拉,认定他有意做戏,撞着胆子说道:“贾化,本官不是被吓大的!”
话音未落,随从书吏嚷叫起来:“了不得了,贾大人撞死了。”
石光珠瞪眼看去,果然见石狮之上漏出一滩血迹,顿时慌了手脚:“快,请大夫、请太医,把贾大人抬进去!”
贾化还撑着:“将军——将军不还——不还欠银,下——下官便死在当下。”
“这贾化倒是有骨气的主儿。”消息传入宫中,太子十分纳罕,“他竟还做过你的先生?早前怎么不听你提到他?”
“果然如此,我头几年就该举荐给你,何必等到今日?”洪淏笑道,“恶豺侍虎,虎壮,豺受驱策,虎病,豺将图虎,贤愚好歹,祸福难料。”
太子含笑点头:“据你所言,今日之事,自然另有隐情。”
洪淏唇角微斜:“这件事,不提也罢,横竖是尽忠为国,当他耿直又有何妨?你抬举了他,有为难事,便是不择手段,他也必能为你料理妥当,只一项,用不得他时,要赶早将他处置才好。”
太子沉吟片刻方道:“既如此,你代我去瞧瞧他。”
洪淏带了东宫赏赐慰劳贾化,贾化认准了洪淏之友便是东宫太子,病榻之上,向他千恩万谢。
“先生放心,明日早朝,言科自有交代。”洪淏谆谆嘱咐,“先生好生保养,等你痊愈,太子亲在御前荐你。”
贾化哪里还记得伤痛,若非洪淏劝阻,立时便要前往东宫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