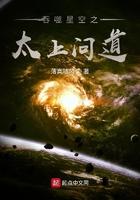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泪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他赶紧躲开目光,但喉结已经忍不住一动。
为了给自己转移注意力,他也望向远山,指着道:“朝那个方向一直走,会到被称为‘太行八陉’的八条横谷,曹孟德《苦寒行》中写的‘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自古是兵家要塞。扼住八陉可断并州到幽州的通路。即便并州失守、大名府失守,只要这几处关隘不失守,就有起复的机会。”
凤栖随着他的目光往远山看了看。她在父亲的书房、温凌的营帐都见过晋地的地图,以往只是一张图而已,父亲和温凌没事也不会和她一个女儿家讲这样堪舆地形,但是现在看着起伏的山,她脑海中那些图仿佛也立体了起来。
“那么,即便并州失守、大名府失守,我们只要守好太行八陉的八处关隘,靺鞨人也有可能被反攻?”
高云桐苦笑:“我们?……我们如今就两个人!只能期待并州失守得不要那么快,让朝廷还来得及调兵遣将来守关。”
看来,他们应当往汴京去,汴京是国都,朝中总有肯听得进意见的忠臣;官家自己虽然好猜忌,但事关国家安危存亡,也不至于还闭目塞听。
“那……”凤栖向南方努努嘴,“按原议,回汴梁报信吧。”
高云桐有一会儿没说话。
“你又不愿意了?”
高云桐叹口气说:“上次谈起,我就没有允诺。汴京朝中诸人,侃侃而谈、朋党攻讦都是好手,但真遇到大事,只怕没有有能耐的。不仅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家或许会忧国因为那是他的国,其他人只怕不会对他们而言,那只是换个主子而已,俯首帖耳,好日子一样是过。”
“朝中不是还有宋相公?不是还有那些和你一样上书请求清佞臣的太学生?”
高云桐苦笑道:“你看看我是什么命数?宋相公又是什么官运?他在枢密院为相这么多年,却只被当彝鼎之器摆放着唬唬人而已,从来不被重用,最后以年老休致赶出汴京。而我我拿自己的一辈子换来的教训还不够么?”
凤栖看着他:“你这就放弃了?”
“不是放弃。”高云桐摇摇头。“流配犯离开军役之地,斩无赦。就是我不怕死,也不能傻乎乎送命去。我也得想想我去哪里才有用处。”
凤栖便也不说话了。他们俩其实一样,都惶惶然如丧家犬。
凤栖想想自家也未尝不是如此:父亲被改藩,肯定会被更严密的监视和管制;哥哥八成会被废,自古没有一个废太子是有好结果的;嫡母和其他家人都在汴京,可是亦没有一个贴心的人可以倚靠她要是回京了,被官家绑给温凌求和都不是不可能!
凤栖落寞地蹲在水岸,捞出一件泡好的衣衫,拿衣棰用力捶起来,仿佛把一腔愤懑都发泄在这捶击之中。
“我来吧,水冷。”高云桐伸手要接洗衣捶。
凤栖肩膀一扭:“我要自己来!”
高云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她。
她好像全是愤懑的力量,一句话不说,一口气把一盆衣服都捶打了一遍,然后把衣服放在溪水里漂洗。书茨
“我想,要不我去投靠郭承恩吧。”高云桐蹲在她身边,帮她把漂好的衣服一件件拧干,“他当然是个小人,但是现在他与温凌交恶,一时间肯定不会投降。现在靺鞨进势惊人,地方上若肯和曹铮一样把这个人用好,说不定能好好地抵挡一阵。他也对我表示过有兴趣,如果我肯去他营中,也许也能说服他一道抗击靺鞨。”
凤栖停了手,好一会儿说:“那我去找我爹爹。”
“晋王?”
凤栖说:“我可不能跟着你投奔郭承恩去,他觊觎过我,万一……”
她顿了顿,又说:“当然,他那时候可能也只是故意这样一说,让官家放松对他的警惕。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找爹爹去比较放心。”
“晋王现在在曹铮身边……”
身份虽然看起来高贵,但谁都知道如今的晋王是谁都可以踩一脚的。
凤栖斜睨着他:“可你不是说过曹铮是个把心思放在做官上的天子信臣,但也算是个君子么?”
高云桐默然了一会儿,点点头:“可以,我先陪你去找晋王,你在你爹爹身边,或许能找到进言官家的途径,我也就放心了。但曹铮不接到官家的命令,是不会与靺鞨作战的,所以我接下来还是要去寻郭承恩,看看有什么及时对付靺鞨的法子,不能真让事态酿到无法挽回。”
可是晋王在哪儿?郭承恩又在哪儿?两个人亦是茫然的。如今困在这样的小山村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尚不知该如何走出这座大山。
另一方面,哪怕仅只是做了打算,也突然就感觉分别在即,突然生出千万种况味来。
凤栖挓挲着湿漉漉的双手,扭头看着拧干了最后一件衣服的高云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