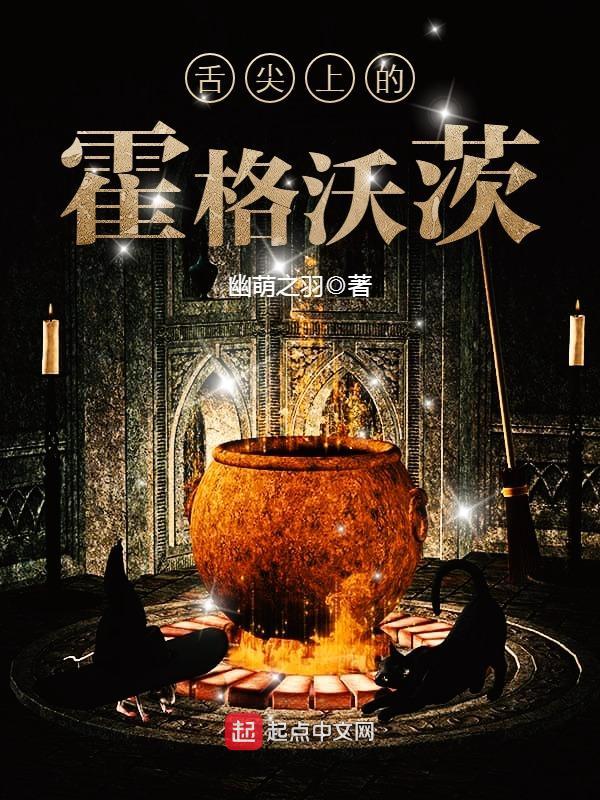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泪 > 第98章(第2页)
第98章(第2页)
然后向上挽袖子,打算把上臂的箭伤露出来上药。
但那农家小媳妇的内衫做的是方便劳作的窄袖,苎麻的粗布也比较硬挺,挽到肘上就挽不上去了。
高云桐看她费力的模样,出语提醒道:“这样费劲,也容易碰着伤口。你为何不像刚刚那样从肩膀处脱出来?”
凤栖看了他一眼:“刚刚叫你占了便宜也就算了,现在你还想占便宜?”
“非礼勿视。刚刚我眼里只有你的伤口,其他什么都没看见。”
那还吻她?还偷看见她背上的伤?
凤栖觉得姐姐何娘子说得对,男人都是嘴巴上道貌岸然,好像正人君子一样,其实都是坏货。
不过确实犯不着和自己较劲。凤栖想了想,还是解开小衫,让他擦药。
有了刚刚浓盐水浸泡的经历,药酒的疼也就能忍了。
胳膊涂完药酒,他又说:“别忙着穿,背上还有淤青,估计你更擦不到,我一起来吧。”
凤栖心里有小小的忐忑,然而他大手温柔,虽也有些薄茧,但丝毫没有碰痛她。
擦好药,他只说一句:“靺鞨人太残暴了,不知他怎么忍得下心下这样的狠手。”
细心地塞好瓶塞,放好药瓶,拉起被子掖好在凤栖肩头:“今日你一定累坏了吧?早些休息。”
山间的夜晚似乎格外阒寂,远处的虫鸣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凤栖和他躺在一个被窝里,浑身都觉得暖洋洋的。但两个人谨慎地分离着,肌肤、手足,都没有碰到分毫。
而且,凤栖觉得他也一直没有睡着,呼吸那么快,那么重。
温凌其实已经算是很能克制的了。虽然婢妾成群,还熟知他军营里最漂亮的那些营伎,但只要他不想被女色所困,就一定熬得住。
身边这位,一直也没睡着,谁知道是不是也在打什么主意?毕竟,一回生、二回熟,孤男寡女、寂寂黑夜,即便是再发生点什么,好像也很顺水推舟。
凤栖怀着好奇心,想看他能打熬到何时。
但她最后自己自己熬不住睡去了,天亮了醒来,看看自己仍是衣衫如旧,而身边那个人早已起身。她披衣挑开一点窗帘,看见高云桐在屋外帮农家劈柴,而且好像在劈砍什么器玩似的,瞄准了,气沉丹田,一柄大斧稳稳高举,抡得浑圆劈下来,木柴整整齐齐裂成两半,接着又是四瓣,像木匠锯出来一样齐整。他好像也很得意于这样的“末技”一样,自己对自己笑眯眯的,露出那月牙似的笑涡。
凤栖觉得这个人真是有意思。动了动胳膊,右臂还有点沉重,但活动无虞,刺痛感也没有昨日强烈了。
屋子里有洗漱的温水,桌上有梳子和一支打磨圆润的木钗。
虽然溶月不在,她倒也没觉得有很大差别。
挽上头发款款出门,那农家小媳妇笑道:“娘子真好看!”
凤栖矜持一笑。
那村妇又笑问道:“娘子不是有夫家了吗,怎么还做姑娘家的装扮?”
凤栖脸一僵,而后说:“这样方便些。”
少妇笑道:“那倒是,你男人很会干活,你有福享。”
凤栖“嗐”了一声,说:“倔驴脾气,又穷又酸,讨厌得很呢!”
少妇抿嘴儿:“男人就没有不讨厌的。不过,能上进、能疼人就好,其他的都不妨碍过日子。”
她直率爽快,接着说:“我得煮猪食去了,你帮我烧火。”
凤栖愣了一下:这么不客气的吗?
少妇毫不藏奸,所以也毫不觉得异常,奇怪地说:“走呀,猪都饿得嗷嗷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