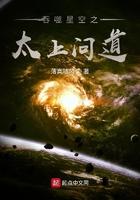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未晏斋的 > 第227章(第2页)
第227章(第2页)
长得好看、技艺高妙的,是伺候主帅、将军这一级别,宴饮上陪酒陪舞,好吃好喝,但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次一等的清秀佳人,是伺候猛安谋克的将官,相当于万夫长、千夫长这类,眠于军帐,只需忍耐一个人的坏脾性;
最惨的是长相粗糙的村野妇人姑娘,多是掳掠而来的,则是平日到晚上就绑在榻上,外头大头兵们排着队、提着裤子一个个轮着泄欲,那种牲口般的羞辱感和痛楚,真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今日这架势,来的人只怕地位不低。营伎中等而上之的都是精心打扮,但也都是愁眉苦脸。
凤栖悄然问:“可知今日谁要来?”
一个漂亮小娘子说:“听说是比冀王还要尊贵的人儿。叫我们务必要好生伺候着,不然当心小命。”
那八成就是幹不思了。
凤栖只是诧异,幹不思也有胆子亲自到温凌军营里来?
又想:他身是太子,又有绝对占优势的人马,拿定了温凌不至于跟他同归于尽,所以亲自过来羞辱凌逼。这样位高一级的压迫力量,温凌纵使恨得牙痒也不能不敷衍着,甚至会不得不退让几分以求自保。
营伎们应差,当然不会有凤栖主仆的事。她们俩也很见机,用草木灰抹了脸,脏布帕蒙了头发,穿灰扑扑的衣衫裙子,只在后头烧火煮水。
熬到夜幕降临,外头篝火燃得半天亮,载歌载舞的声音响起,军士们喝酒说笑声也响起。
凤栖盯着小铫子下的火苗,怔怔地发呆。
只听萨满的傩歌高亢了一阵,又渐渐低矮了,觥筹交错声清晰起来,接着又是歌女们的唱腔乍起,渺渺入云,再接着是鼓点,节奏和调子有些像《臻蓬蓬》,踏歌的欢声又雷动了。
纷乱的脚步声却从四周纷至沓来。
凤栖在这些声音里辨析,渐渐心往下沉,终于说:“溶月……”
溶月没她那么细心敏锐,一直只专注于火焰的大小和铫子里的沸水,“啊?”了一声抬头:“娘子,怎么?”
凤栖说:“他们在营地里搜查。”
“谁?搜什么?”
凤栖说:“今日来的,不是郭承恩,就是幹不思自己不,以规格来看,是幹不思的可能性更大;幹不思肯定没有怀着好意来,在营中搜检,想必是要找到什么证据。我们很有可能也是他要搜检的内容之一。”
溶月张大了嘴,好半天才说:“我们逃罢。”
“往哪里逃?在这营地的哪里,他们都能瓮中捉鳖一样。”凤栖说,“越动弹,越显眼。”
溶月害怕得开始落泪、哆嗦。
凤栖抓住她的手:“溶月,冷静,该来的总会来。”
溶月也点点头:“娘子,我不怕,我与你一起。”
凤栖拿了一块炭木,翻开白苎麻的裙子,想写最后的遗言,又陡然想到写了也不一定能流传出去,大概她上次给高云桐的信中暗书,就是她此生最后的遗言了。
但现在总要留点什么,给后人,亦或自己。她再一次握紧炭笔,看着裙褶一道一道,宛如竹纸上打着朱丝栏。
“溶月,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家人说的话?”
溶月流着眼泪,摇摇头:“家里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呢,何况写了他们估计也收不到。”
凤栖笑了笑:“不错呢,是处青山可埋骨,胡乱用草席一卷,挖个坑就算客气了,就不知道有没有人为我们‘夜雨独伤神’。”
知道溶月听不懂,只抚慰地拍拍她的手:“不怕,来了也好,我们都是干干净净回去。”
又想起温凌那个可怕的毛病,自己也不由打个哆嗦要是她也被他分尸斩首,腌制得面目如生,藏在匣子里随时拿出来盘玩,该是死都不能安生了吧?只是她心思怪异,又与寻常小娘子不同,突然好奇起来,若是人真的死了,她死亡的头颅又能不能像伍子胥挖眼置于东门一样,还能看到眼前的一切?
好奇心一起,好像害怕又少了。
她手速如飞,在裙子的米黄色里子上用炭笔写着一笔行草书,然后放好裙摆,默默听着外头的一片混乱声。终于有人掀起了她俩所在的帐篷门帘,然后用粗鲁的靺鞨语大声喊:“快来!这里还有两个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