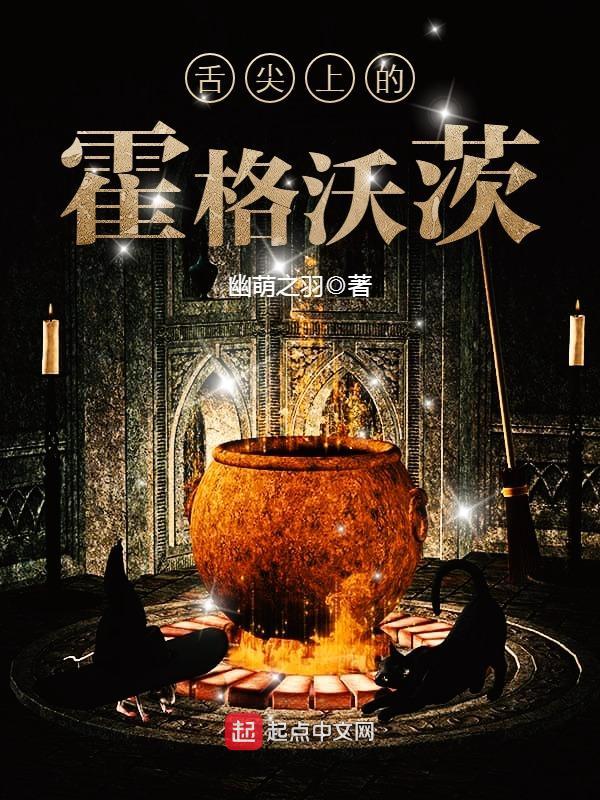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未晏斋的 > 第156章(第3页)
第156章(第3页)
他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只能把她用力揽进怀里,喃喃道:“卿卿,这里面你没有半分错!我们一起想办法,看能不能为你爹爹正名。”
凤栖摇摇头:“或许吴王就是天命所归呢?”
被他用力抱着,好像有点呼吸不继,她挣扎了一下:“我困了。”
“好,早点休息。”
但她到了床上,困得脑袋发晕,眼睛酸胀,可心里无数的声音涌上来,自己都分辨不清自己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只觉得每一根血脉都滚烫地流动的,无数人在她脑袋里狂呼乱喊,嗤笑她和她懦弱的爹爹,又及她那卑贱的姐姐……
“我睡不着,嘉树。”她也喃喃的,“我好累,但是我睡不着……”
他唯有凝望着她闭着眼睛喃喃说话的的模样,小心撩开她的额发,轻拂她的脸颊,又用手轻轻地、有节奏地拍她的后背,然后给她吟诗:
“曾几慨然谈时事,
书生意气誓驱胡。
却看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①”
她听得嗬嗬地尖刻笑起来:“高云桐,你曾经那么迂的么?你在说你也有和我同病相怜的遭遇,为人不知,乃至落入尘泥?”
高云桐拍着她,随着那轻柔的节奏缓缓说:“是,我曾经那么迂腐、愚蠢,满心意气给人丢进字纸篓。其实我在被褫夺功名、逐出汴梁时写这首诗,也是满心愤慨的。但是如今我明白,这条迂腐愚蠢的道路我还会矢志不渝地走下去,这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使命。”
“不为凤家王朝?”
他斟酌着说:“嗯。甚至,也不是为你。”
这话听起来十分无情寡义,绝不是满怀甜蜜幻梦的摽梅女儿家爱听的情话。
但在凤栖心中,却如大鼓击响心扉。
她突然胸腹中激荡起来,那憋着的痞块在被巨大的浪潮冲击着。
那浪潮如忻州城外那条春汛起浪的河流,淹没了她,又洗涤了她,那种鼻中酸胀、咽喉窒息的感觉突然被冲破了,眼泪哗一下奔流出来。
凤栖埋首在高云桐的胸膛里,终于尽情地大哭了一场。
他们都是到后半夜才睡着,但又很早就醒了。
醒来后都是先转向枕边那位,互相小心翼翼地瞧着。
高云桐说:“你看你眼睛都肿了。”
凤栖说:“觉着了,睁不开了都。”
高云桐说:“几件衣服我有空去洗掉吧,你这一对眼睛,一定惹那些村妇发问。”
凤栖说:“不必了,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去洗。这里的风俗都是女人躬操井臼,要是你一个大男人还去洗衣服,只怕他们都要笑话你。”
“我才不怕他们笑,以前在京城一个人呆着读书时、在并州军营里做事时,难道不都是自己洗衣做饭的?男人又不是傻子,洗衣做饭学不会的?”
凤栖说:“他们以你为主帅,但毕竟又是没读过什么书的乡里人,肯定有一肚子的偏见,入乡随俗,我也不至于洗不动几件衣衫。一会儿先用热水熥一熥眼睛,晚些找个人少的溪流去洗就是了。”
高云桐只能说:“好吧,这几天操练不能断,我得先去了,早餐我给你带回来。”
凤栖跟着他过这样有烟火气的日子,心里略平静了些。
坐在窗前用热手巾焐眼睛,心里对父母还是十分担心,此刻倒宁愿吴王凤震如宋纲所以为的那样还是个仁厚之君,至少给父亲一条活路;又盼着父亲在汴京坐镇当皇帝的这段日子没有犯下什么让人拿捏把柄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