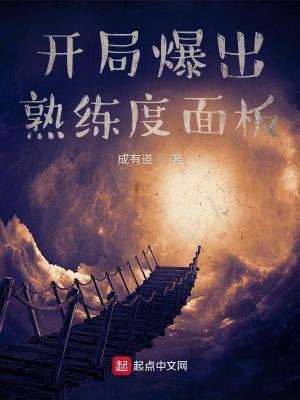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泪电视剧免费观看 > 第201章(第3页)
第201章(第3页)
章谊露出玄之又玄的神情,笑道:“曹铮叛国,都‘莫须有’了,晋王岂不能‘莫须有’?”
温凌明白过来,这晋王想是遭了忌,被哥哥借机处死。
从冷血政治人的角度来说,温凌很明白这事的合理,但想到刚刚凤栖的神色,又想凤霈不过是个懦弱无能之辈,主动让位给哥哥凤震,凤震犹自要杀他除根,看来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并非可以轻易搓圆捏扁的。心里不由对凤震产生了几分警惕。
他闲闲问道:“那么,难道你们对皇帝的亲弟弟,也用披麻拷逼口供?”
章谊道:“那倒不至于,说实话,我们那位晋王,估计连两记鞭子都受不得,也不需要动这样的酷刑。只不过曹铮伏诛,很多人不服气,也有人跟我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他浑然不以为耻,“呵呵”笑两声道:“晋王声名狼藉,在晋阳就是花花公子一个,登基时得位不正,是天下笑柄,迫于天下清议退位,却又在后宫盗兄长之妾,如今孩子都生下来了,他这乱了纲常的臭名已经妥妥地坐实了。”
温凌虽对“得位不正”四个字不大满意,但讲到后面的“盗嫂”丑闻,倒又不明白且好奇了:“等等,这又是怎么回事?”
凤震本来就打算着一石二鸟,一头是除掉曹铮这个尾大不掉的建节将军,一头是除掉弟弟凤霈这个前任皇帝。
但大梁以礼法治天下,没有罪名,即便是皇帝也不能滥杀。
温凌催逼他杀掉曹铮催逼得紧,凤震当然也头疼了很久。大理寺先是不得力,不肯动用重刑,换了几个推官,甚至最后胁迫到大理寺卿本人头上,才终于沿用了章谊举荐的酷吏,对曹铮动用了史无前例的“披麻拷”。
曹铮痛得半昏厥时在供状上画了“十字”花押,但醒来之后,听闻自己被处以斩决,神色平淡,甚至带着冷笑。
转天,曹铮蒙冤的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官家急怒,但即便是皇城司明察暗访,也没有查出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接着,太学生砸了太学,伏阙为曹铮请命;再接着,京中不少官员上辞表,不愿再为官;百姓们更是喧嚷,说曹铮何曾有半分反迹?何况外敌当前,只有曹铮、高云桐能抵御二三,现在杀曹铮岂不是自毁长城?
再接着,各地上书、招贴雪片般往京城飞,大多都是为曹铮求情、说话。
这架势,皇帝也不大招架得住。
所以,凤震愁眉苦脸,悄悄召见了章谊:“这可怎么好?骑虎难下了!不杀曹铮,别说靺鞨冀王那里通不过,就是朕自己又该如何收拾残局?难道还让曹铮继续当他的枢密使?”
章谊道:“官家!斩草不除根,日后哪怕是贬曹铮出京、流放边远、永不叙用,也必然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何况冀王口口声声必要曹铮的头颅,这老贼相貌有特色,想砍个假脑袋蒙混过关都难!”
“我何尝不晓得!”凤震道,“所以才找你商量嘛!”
“大家嚷嚷着要释放曹铮,无非也为两点。”章谊分析道,“其一,曹铮罪行不大明确,叛迹不够昭彰;其二,大家都怕再和靺鞨打起来,没有了曹铮,北方防线上缺少得力的将才抵御。”
“唉,可不就是!”
章谊当了多年相公,老辣确实是老辣,他笑道:“第二点,官家不必太过犯愁。北方缺少将才不假,但如果不打仗,有没有将才又何妨?如今和议成功在即,一旦谈成,无非是给点钱,割点地,都是可以承受的损失,以后大梁和靺鞨两国就如同当年大梁和北卢两国一样,岁币到位,再开边贸,从此只管赚钱,再无战乱。”
凤震仍然皱着眉听。
章谊当然知道他的心事,笑道:“若是官家担忧,杀曹铮之后,臣愿为官家分忧,镇守并州。”
凤震心中顿生狐疑,但脸上笑道:“若爱卿肯担这重任,那倒是让朕无比放心了。”
章谊道:“臣本当效犬马之劳,和谈若成,臣在靺鞨人面前也有三两功劳,还是能说得上话,保得住边境安泰的。”
凤震问:“但是第一点怎么办?口供画押都拿到了,怎么还有这么多闲话?”
章谊道:“其实官家不必担忧这些闲话的。”
凤震摇摇头:“不然。朝野舆论,轻微时不用担心,甚至能造成党同伐异、互相制衡的局面,于为君者也未尝不是好事。但如今只有你我等亲信臣子还坚持曹铮有罪,余外这么多人都言曹铮冤枉,众口铄金,我们君臣何从自辩?说实话,你那句‘莫须有’,确实不能服众!”
章谊嘴角一抽,急忙低头掩饰,拱手道:“官家说得极是。”
心里想:谁叫你得位不正,大家不服气你呢!
而凤震心里也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先靠舆论扳倒了弟弟凤霈,他算是见机,没敢和我硬杠,乖乖让位,省了我不少麻烦。朝野舆论当然有覆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