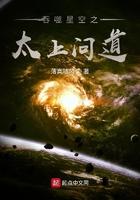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三侠之红拂女 > 第167章(第2页)
第167章(第2页)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于北卢、于南梁,都是如此。
如今这些纵横交错的沟渠重新被疏浚,就如同河东河北山野间的义军,人数虽然不多,但一点点蚁聚起来,便是偌大的力量。
两个人在山顶极目开阔,心情也开阔起来。
高云桐觑见士兵们各个分布在山腰、山脚各处,便悄然探手,握住了凤栖的手。凤栖娇作地扭了扭手腕,但随着他稍一用力,便也驯顺地被他握牢,手背上覆着他的暖意,心里也暖暖的了。
凤栖问他:“靺鞨一直按兵不动,似乎在等待什么。咱们有没有新消息?若是靺鞨真的内部虚弱,不妨出动出击,攻其不备。”
高云桐说:“派出的斥候递来的消息,靺鞨的太子和冀王好像没有内讧的迹象,不过现在一个驻东,一个驻西,时不时互通来往,则都是由一个勃极烈监军一般。”
“娉娉那里有没有新消息?”
高云桐脸色有些暗:“没有。”
他缓缓地摇摇头:“有好一阵没有她的消息了!曹将军派骑兵偷袭幹不思的事,我后来才知道,阻止也晚了,最怕就是幹不思实则是在下套,那么娉娉就危险了。”
凤栖便也有些失色:“能不能打探到她的消息?”
他又摇摇头:“她一直深入敌营,是温凌的枕边人,别说我们这方的斥候,只怕除却温凌的亲兵,也极少有能见到她一面的人。消息大部分都是她单方面传给我们,我们的消息都无法到她手里。”
他不由叹口气:“她这样子的艰难,简直不可想象!”
“所以,谁说只有贞洁烈妇才是好女子。”凤栖亦太息道,“奇优名倡中,从来不乏真君子、真列女。可惜,都很少能让世人看到。”
谈了一会儿,又聊到接下来的策略。靺鞨蜷缩不进攻,也不算坏事。他们没有那么长的补给线,所以军需大多从河东河北百姓处掠夺,少不得竭泽而渔,所以已经是怨声载道,两处遗民没有不憎怨的;而渔猎为生的靺鞨人,在中原看到这么多的富庶,眼也热了,心也懒了,跑马圈地自己却不会耕种,所以仰赖的还是汉人的耕种,却荒废了他们原本的渔猎本领。
“靺鞨不得民心,必不长远。其实你三伯主战不主和,我还是认可的。”高云桐说到这里,小心看了凤栖一眼,“当然,他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心思,还待再观察;你爹爹,最好也能离开京城,让他就藩去,大家都放心。”
凤栖闷闷地“嗯”了一声,说:“曹将军是已经得到好几块金牌,命他出击靺鞨,收复国土了。曹将军很为难,一则他身子骨还未恢复,二则其实全面反攻实力还是不足的,现在这位官家但知催促,却不见有一颗粮食往这里送,曹将军还得从并州经滏口陉调运粮草,更是像被扼着喉咙似的。”
在江南纸醉金迷之后,再当如今这乱世的官家,凤震只怕还是纸上谈兵的多。
高云桐只能寄望于曹铮和宋纲,说:“希望他能够听取谏言,不轻举妄动吧。我也上书给他了,提了些建议,传旨过来是大加赞赏,但是也就只是赞赏。我想要的对抗铁浮图的钩镰和长矛,却推说京里要慢慢打造,叫我们自己先想办法。”
正说着,一个斥候被带上来,递过一封插着鸟羽的信。
高云桐接过信问:“你是从河北来的?‘豆蔻’那里的消息?”
问完就知道犯傻了何娉娉那里递出的每条消息都是带血的,不可能轻轻松松拿信封装着。
那斥候摇摇头:“我是从幽州来的,是沈相公那里的消息。”
“相公?”高云桐不由失笑,“已经这么重用了啊?”
斥候道:“是很得重用,靺鞨的君臣,很多对汉人的典章制度、诗词歌赋都感兴趣,当然也有深恶痛绝的,反正那位蛮酋皇帝是很看重沈相公的,官职一升再升,还说要把一个靺鞨贵族的女儿嫁给他。”
高云桐瞪眼道:“他答应了?”
“暂时还没有,不过已经逼得很紧了,不知道他还能熬几天是那个靺鞨的贵女新寡思春,瞧见了他击檀板唱词曲的样子,喜欢得不行,又没什么廉耻羞臊之心,一直主动黏着他呢。”
“好家伙!”高云桐摇摇头,“桃花来了,挡都挡不住!”
气氛便也随着这个八卦的消息变得轻松愉悦起来,他微笑着撕开密封的信封,抖开信纸细细看。
但他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了。刚刚还陪着他微笑的凤栖端详到他的神色,不由有些紧张:“怎么了?幽州那里有什么不好的消息?靺鞨人打算增兵?进攻?杀我七伯?……”
高云桐摇摇头,把信纸递给她:“沈琅玕很紧张,说传来消息,有潜伏的人被发现了,幽州那里也收紧了对汉人的管辖。他要我有机会去把他在润州的父母妻儿转移到其他没人晓得的地方去。”
“啊!娉娉她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