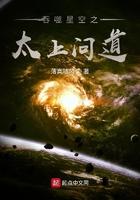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三侠之红拂女 > 第124章(第2页)
第124章(第2页)
沈素节叹了一口气:“是啊,江南富庶之地的吴王,本来就隔岸观火,在最危难的时候也不肯出兵出钱襄助官家;现在到他头上搜刮钱粮,他自然不愿意;不仅不愿意,晋王是庶九子,被敌人推举为皇帝,身为庶三子的吴王想必更是气得切齿,一直没有肯承认弟弟的皇位。只怕有大文章好做了!”
“咱们也不能慢慢等待时机了,时机得自己开创。”高云桐撮牙花子说,“知不知道上次那曲《凤仪亭》,何娘子听懂了没有?愿意了没有?”
“你呀,真是个无情!”沈素节批评他,“她肯定听懂了,也肯定很难过。心心念念都是你,你却让人去使美人计!”
“我……”高云桐瞠目道,“她怎么心心念念都是我了?”
不错,与何娉娉近距离接触过两次,并州那次,心会神交。
他要非说对何娉娉的意思一点看不出来,那也真是装傻。但说他有心,也真谈不上。
沈素节见他微微蹙眉不说话,笑道:“你那么聪明的人,又不是真木头。小娘子家的心思你还不懂?喜欢上了你,为你赴汤蹈火她也心甘情愿。你不如哄哄她,她就能主动推进这件事了。”
高云桐闷闷地说:“若为了让她赴汤蹈火而欺骗她,我做不出来。”
“咦,怎么又这么迂腐了?”沈素节说,“欲成大事,这点子欺瞒简直不算什么。”
高云桐说:“不错,都说无毒不丈夫。可是我还是做不到。我希望何娉娉和我们一起拯救大梁,但不应该是骗着她去做出牺牲牺牲,必须心甘情愿。”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豆蔻梢头真国色,但念一心谁?
其恨已绵绵,无力复相思。只愿君心似我心,遥望一江水。”
他拿起笔在粉垩的墙上提了一首词,掷笔道:“国仇家恨当前,无心谈情。她应该能懂我的意思,让这里的歌姬把曲子唱开来,她总会听到。”
沈素节在他身后长叹一声。
高云桐拱手道别,出了酒楼,牵着马却在一处僻静地方倚着墙。
嘴里坚决不谈“情”,可是心里深埋着。
刘令植挑唆南梁内讧,凤霈和凤震两兄弟又要来一次阋墙内斗。
高云桐在江南时,吴王凤震已经就藩。就藩头三年,与地方上客客气气,人人称道这是个“贤王”;第二个三年,吴王锋芒渐露,对付那些违拗他的人毫不手软,纵使先帝对他的上书弹劾多有驳斥,吴王也总有手段让自己得偿所愿;他在江南藩地立定脚跟之后,先帝去世,官家凤霄登基,江南虽服从统领,年年表贺、乖乖称臣,但是又特立独行,并非事事都受官家钳制。
官家自然晓得这个哥哥的德行,既抚慰,又打压;既不能有挤兑兄长的嫌疑,又不能让凤震太过嚣张。总算这些年深谙平衡之道,江南二十八郡太平无事。
如果老谋深算的吴王凤震,与软弱无能的新君凤霈争斗起来,吴王占据地利人和,很有优势。
高云桐一是担心内讧会使得南梁愈发虚弱,二是担心百姓会在这样的内斗中继续受苦,三则是隐隐害怕凤霈败落,则覆巢之下无完卵。
凤栖像他心中遥远的美梦,时时念及,恍惚间觉得美好得不真实一样,但一旦离开梦幻似的恍惚,而来到残酷的现实里,她就成了拴在他心尖的一丝线,紧紧地把他的心吊着,既酸且痛,既痛且快,既快且忧……
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完,他要带着他的人马回到汴梁,保卫他的家国,保卫他的月光。
高云桐的唱和之作,很快通过歌娘的曲儿传到了何娉娉的耳朵里。
她在无人的时候,躲在床上“午睡”,咬着被子不让自己哽咽出声。
她自小儿就学习各色技艺,也很早就通晓讨好男人之道,十三岁刚刚长成就被“破瓜”,给教坊司赚了好一笔“梳拢”的银帛。
按说一次秋波暗送,对方没有接招,再正常没有,她素来冰山似的以冷漠换得男人们的痴狂,却是第一次感觉到入骨的羞耻。
她心里绝望地想:我是勾栏贱籍,迎来送往、人尽可夫,他必然是瞧不起我!
又想:他现在带着刺配的青印,和我差不多低贱,他又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呢?
想得咬牙切齿,狠一阵、怨一阵、茫然惆怅一阵,眼泪流得枕头都湿了。
不知哭到何时,天昏地暗间,突然听见外面的丫鬟在敲她的窗,小心翼翼问:“何娘子在里面吧?大王回来了,在寻您呢。”
何娉娉慵慵地翻身起来,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光线昏昏然,也照不清楚,隐隐见颊上晶莹,就胡乱抹了两把,也懒得重调胭脂水粉,只把头发重新挽了挽,堕下一半就插支玉梳。然后披上一件水红色的褙子,趿拉着家常的鞋就到后面伺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