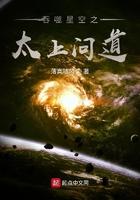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仆仆的意思 > 第142章(第2页)
第142章(第2页)
她只能叹口气,说:“但愿你看得准。”
“目光要长远是不错,但也需先看准眼下。卿卿,你看”
高云桐觑着她表情平静下来了,于是上前轻轻揽着她,任凭苇絮拂过他的面庞,望着河面轻声低吟着: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浪交涉亦难为。
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1)
凤栖嗤笑一声:“怎么,你还打算仗打完之后马归南山?”
“固所愿耳。”他笑道,“朝中若能给我留个在翰林院修书、御史台谏言的位置,也很好;或者能放我到地方当一任知府,造福百姓,也很好。我又不是生来的武将,不过形势逼迫罢了。将来,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能发一分光与热,或能留一身清名独自悠游,都很好。”
扭头问:“哎,你笑什么呀?”
凤栖说:“笑你骨子里还是个腐儒。”
他收了笑容,但神色依旧散淡:“腐儒就腐儒吧。这个世界上功利的人太多了,需要一点腐儒来坚守底线。”
高云桐自然而然地随着她的目光远眺:“亭卿,我知道你的为难,我也不是就已经信赖了吴王。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要把外虏打出我们的国门,最好打得他们再也不敢来。然后收拾山河,整顿防务,也改革以往那些弊政。这样的艰难局面也在筛选:筛选明君、筛选能臣、筛选干将……等一切平复了,我就带你回老家阳羡去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过自在平静的日子。”
凤栖垂着头,半日说:“估计那时候我们都七老八十了,跟你回去我可种不动地!”
高云桐笑起来:“这场仗怎么会打几十年之久?我看靺鞨不过是一时幸运,未必能撑过五年,绝不可能撑过十年!再说,你跟我回家去,哪个会舍得让你种田?”
“那我跟你回家去干吗?天天在家吃干饭?”
“赌书泼茶,儿女绕膝,闲来就云游山川、溪畔垂钓……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口中刻画的图景是真美好,手也自然伸过来握住她的手,把他的希望和勇气渡给她。
凤栖却也不全信,只是心情平和多了,望着奔流的淮水,摘着手边枯萎的苇絮。
她垂头心想:他和嫡母周蓼不一样,他并不是一概的迂腐、不通庶务,他只是活在理想里,且在他的理想里活得毫无畏惧。
理解了他的想法由来,她不由又抱愧地看了他一眼。高云桐却似乎没有在意她刚刚毫不客气的言辞,而是笑眯眯地望着淮河的远方,看那波光粼粼的河水和那一望无际的芦苇滩涂。
凤栖自知要改变一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何况他的观念也没有错误。
只是,她也没有想到,他们都会因这一时理想的美妙,而把自己陷入深深的阴暗的旋涡里。
这番彻谈之后,两个人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还是有了默契,黄昏时又乘马回到了驿站所在小镇,就在街边一人吃了一碗热馄饨,听着馄饨摊边的人们热火朝天地谈着如今的局势。
“听说,和靺鞨又要打起来了?”
“是啊,我在邓州的亲戚已经逃回来了,说靺鞨兵极其厉害又毫无人性,不逃肯定没有命在。”
“邓州不是已经划在割让的土地里了吗?这次打仗还会波及?”
“在靺鞨的领地里,升斗小民过得哪有半分尊严可谈!”说话的那个端着一碗浊酒,摇摇头说,“本来就像奴隶似的,不敢有半分违抗靺鞨人的徭役和摊派;鞭抽杖打,都是稀松平常;那些蛮夷看上了谁家的姑娘小媳妇,毫不顾忌人伦,抢走玩够了再送回来,甚至就不送回了。”
“天哪!到底是教化缺失之地,这陷于敌手的土地和百姓,过的是怎样水深火热的日子啊?!”
“所以才须得往南边逃嘛。逃出来也不容易啊。”
“只能逃?就不能一战?”
“听说河北各地有义军在作战,很让靺鞨头疼。但是毕竟只是义军,”说话的那位摇摇头,“要是朝廷肯组织起来,发布诏令号召天下为收复土地与靺鞨作战,肯将义军的领袖封个将军、宣抚使、节度使什么的,乐意为国效命的人一定会更多。”
“你乐意不乐意呢?”
“我乐意啊!不过我瘦得没劲,上战场拿不动刀。”
另一位凑趣开玩笑:“没事,也不一定非得上战场拿刀动枪的,据说打仗特别费钱,打一套札甲起码是五十贯的价格,一副好弓箭也得十贯,你就把一半家资捐了,虽然买不起一副甲,应该还买得起半副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