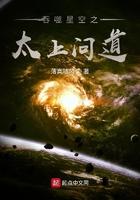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仆仆的意思 > 第107章(第2页)
第107章(第2页)
他手一劈,做了个“单刀直入”的动作,眯了眯眼睛,显得智珠在握。
“这……行吗?”
温凌徐徐说:“汴梁,才是南梁的根本,不得汴梁,过了黄河也守不住;得了汴梁,黄淮均是不取自下。咱们兄弟齐心,直奔其国都,就如运臂取物,回手即可得。反之,在并州、磁州等地慢慢围城攻袭,待南梁做好准备,勤王之军四下赶到,胜负谁又能预料?!”
幹不思犹豫了一会儿。
他当然不愿意攻陷汴梁的功劳被哥哥分去。但是原以为南梁军民都是泥糊的,一打就稀烂,哪晓得居然和想象中不一样,南梁战力不强,但一旦反应过来了,却很有韧劲。幹不思是父母的宠儿,其实不如温凌能吃苦耐劳,胶着之势让他心里也焦灼,恨不得立刻功成,抢南梁一批好东西回去享受战果和战功。
本来他一心想着借温凌的刀把磁州取下,但明显温凌没肯答应,但愿意和他一道去打汴京。
于是他心里又想:温凌不就是想抢功!也好,这会子拉着温凌帮忙,等拿下汴梁之后再给父汗发战报,正好可以问问温凌在并州打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折转到磁州来了?即便父汗见温凌有功不罚,但赏赐肯定也没有,这太子之位自然也轮不到一个不服从命令的皇子头上。
想明白了,幹不思点头笑道:“有道理。”
温凌微微一笑,转动着拇指上射箭用的扳指。
他当然有他的私心,确实打算和幹不思抢一抢攻取汴梁的功劳了,台面上的话当然也要说得漂亮,不至于现在就撕破脸。
酒足饭饱,幹不思推了两个侑酒的小娘子过去:“阿哥,这算是这批农妇中的翘楚了,你别嫌,等到汴京咱们再挑好的。”
温凌目光扫视着两个小娘子,她们害怕得发抖,半透明的丝衫透出来的皮肤上都起了粟粒。他捏起其中一个的下巴抬起来,那脸确实还算端正,可目光畏怯,好像都要哭了。
“没意思。”他说,“睡这样一个女人,我觉得我吃亏了呢!”
幹不思大笑起来:“阿哥,你确是长得好看,可也不必这么自负嘛。你不妨就让这两个小娘子占点便宜嘛!难道你还念着你那作死的王妃,准备打光棍来追悼她?”
温凌顿时脸色一懔。
幹不思看出他不高兴,仍是满不在乎地笑着:“两个你若是不行,就一个吧。一个,你总弄得动吧?”
“浑说什么!哪个‘不行’?”温凌恨恨地瞥了他一眼,也不再言声,伸手“嘶啦”一声,扯开了其中一个身披的薄纱衫子,肚兜也一把撕下抛到一边,裙带一拉,女子趔趄得几乎站不住,那湘江水一般的丝裙流泻于地;紧跟着又是另一个的。
两个女孩子色相毕露,害羞地捂着前胸呜咽着哭起来。
他心中有了些微的快意,问:“哪个是处子?”
幹不思道:“都不是了,在军中呆了这么久,还留个处子干什么?不过是一件玩器罢了,还等着做侧妃啊?”
温凌被弟弟激怒,便也没有了半点怜惜。
自从温凌的海东青旗出现在磁州城外,凤栖为防着忻州她巡城时被温凌发现的事再次重演,一直没有敢在城墙露面。
且自从温凌到了城下,靺鞨军一次都没有和磁州死磕,川流不息的军队只在城下威胁,过了几日,就听说大军已经拔营了,只留了数千人在外城扎营,目的是看着城里的人,不让出去联络报信。
凤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对知府杨泉吹嘘道:“你看看我这个女儿,巾帼不让须眉!几条妙计打得靺鞨不敢恋战,现在一路南下去了。”
杨泉陪了陪笑,接着继续愁眉不展:“唉,接下来估摸着靺鞨军要往汴京去了,我虽让人用蜡丸裹了战报送往京城,但是现在派出的斥候十个都不一定有一两个能够出靺鞨人的封锁圈,这些消息不知京城到底得到没得到?”
凤霈完全没有他的忧国忧民,心里只寻思自己:汴京要攻破其实更为困难,但是吓唬我那哥哥一下又何妨?靺鞨只是马上蛮族而已,并无能力治理中原,迟早要退回去,但不知退回去的时候是否已经餍足所欲?会不会还要围攻磁州?磁州这里又安泰不安泰呢?
倒也想念自己的家人,上次他故意激将,逼得曹铮说出了消息:儿子是被贬为延陵郡公,发往吴地,倒是因祸得福;只是妻妾和女儿们都在汴京,嫡长女还嫁在京中,不由得不牵挂。
因此,当他看见凤栖的时候,叹息着说:“亭卿啊,咱们这里暂时是平安了,但京里的情况我还是担心得很。我寻思要是官家识趣,肯与靺鞨议和就好了靺鞨这种荒蛮之地的酋首,能有什么见识?无非想要钱粮、土地,想不用游牧辛苦就可以安安稳稳吃饱饭。想我先朝割幽燕、给岁币,与北卢成兄弟之邦,和平了百余年,不也是大幸?”
凤栖瞪着眼儿说:“靺鞨和北卢可不一样。北卢和我朝那时候是各有胜负,再打下去两败俱伤;靺鞨现在一路高歌猛进,我们签城下之盟还能有好果子吃?即便是要和谈,也还是打几场硬仗才有谈和的资本。”
“你看你女孩儿家家,怎么说起打打杀杀眉都不皱?”凤霈皱起了眉,“当然,我也就自己一说罢了,官家也听不到我的想法。”
他一边害怕战事,一边又闲极无聊,隔了一会儿又问:“亭卿,你的琵琶技艺生疏了没有?弹首曲子给爹爹听听吧。”
凤栖没好气说:“兵荒马乱的,姐姐留给我的琵琶早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还弹什么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