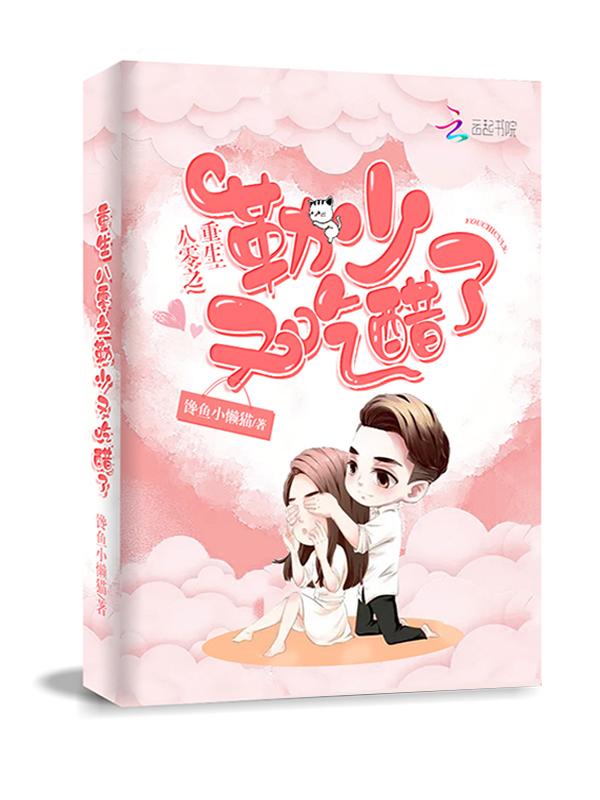奇书网>凤尘是什么意思 > 第210章(第3页)
第210章(第3页)
虽然是行军,但靺鞨军队习惯于将金银细软和随军的营伎等都带着,免得地盘被别人包抄而一无所得。
温凌确实检点过粮草,其实算不上“够够的”,但靺鞨军有打草谷的习惯,河南未经大战乱,也还富庶,加之还有好多女人和签军,不行还可以吃人肉撑过去。
但当斥候告诉他第三拨军队已经被太行军截为三段,困在黄河北、黄河南和黄河之上时,他还是大吃一惊:“那支土匪军有那么多人?!”
斥候说:“密密麻麻的好像都是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多!”
姝次
温凌心里一紧:“领军的是那个姓高的贼囚么?”
“应该是。”斥候说,“都打着‘高家军’的旗号,没有统一的军装,但都是蓝色半臂衫子,白色范阳笠。”
温凌不由看了看远处的汴梁城墙。
辎重一般都放在后队,铁浮图虽强悍,野战几乎无敌,但要攻陷城池不行,除非凤震和凤霄一样使用六甲神兵的昏招,最后被迫开城投降。
他现在相当于孤悬在中途,前进无望,后退也危险。
只能叫斥候继续打听清楚,看看太行军到底有多少人马,是怎样的组成,是不是虚张声势,然后才能判断下一步战略。
只是心里顿然紧张多了。严命前队和中军的队伍就地驻扎,结成层层重帐网城。每日不仅反复操练,而且马匹川流不息布置疑阵,也探好了线路,随时准备撤退。
凤栖当然感觉到不对劲。军队停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好些天没动弹;每日操练虽紧,却毫无前往汴梁包围的动向;最重要的还是温凌的脸色:他开始几天都没顾得上到凤栖这里来,后来来了,也不问她身子怎样,只是过来喝几盏闷酒,有时候要听她弹《将军令》给自己鼓劲,然而听完铿锵的琵琶曲,还是愁眉不展,甚至有一回问她:
“将军若是落败,是不是就一文不名了?”
凤栖很想拿“自古名将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类的话来刺激刺激他。
不过恶毒的话到嘴边,还是终于忍了下去,只说:“青史总会留名的。你看李广难封,时运不济,但还是叫人世世代代敬佩他,对吧?”
温凌稍微好受了些,也觉得她近来脾气改观,不再把他当敌人了,于是也试探着说:“留名有什么用呢?我们靺鞨又没有修史书的习惯。我还是希望我能赢得这一局。”
凤栖瞟他一眼:“那你也不必对我说。你又信不过我,我又不懂军事。”
埋头忙自己的针线活。
温凌看了看她缝补着的衫子,突然伸手解开了她身上那件襦衫的系带。
凤栖顿时一惊她已经不再流血了,小月子的时日也结束了如果温凌想玷污她,她已经没有理由推辞,只能拼死反抗或者乖乖就范。
所以她不觉就用手掩住了前襟,呵斥他:“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
脑子疾速地运转着,考虑自己是选择拼死反抗还是选择乖乖就范。
温凌毫不客气拨开她的手,定神凝视着她穿在襦衫里面的红色肚兜。
之后问道:“你这件亵衣,高云桐见过么?”
凤栖低头看了看,这是那件用垫点心匣子的红缎做成的肚兜。
她不知道温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敢贸然作答,只说:“关你什么事?”
温凌抬起的眸子冰冷而凛冽,过了片刻说:“我想剁你的手指给他送去,但想到你缺了手指,该如何给我弹曲儿呢?”
又打量了她的脸半天,打量得凤栖毛骨悚然,才又说:“也不是不可以割你的耳朵,或取其他部件。但我有些不忍心你那么痛苦,留下永久的残疾。”
凤栖咽了口唾沫,半日才讲:“你想拿我吓唬高云桐?”
“嗯。”温凌点点头,“不知道他对你有几分情意?也不知用你的肚兜羞辱他,他会冲冠一怒、使出昏招,还是会为了你暂时服从我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