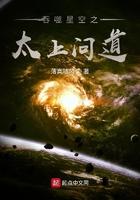奇书网>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 > 第122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第1页)
第122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第1页)
“没事,王叔就是来告诉你,你放心大胆放手去干,王叔给你守着玉璧关。”赵瑾膝下无子,又少年时就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磨砺,造就了一身杀伐果断、雷厉风行的性子。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流露出长辈对晚辈的那种关爱。虽然那一闪而过的情绪极幽微,表达的方式又太过刚毅,甚至难以捕捉。但那一瞬间,他终究是真的流露出了那么一星半点的真情。赵瑾这时候,终于真正地接受了赵宁的身份,也不再怀疑他的身份。他没有多说废话,出了王宫直奔玉璧关而去。赵宁有些愣神,赵瑾都走了半天了他才后知后觉回过神来。夜里赵宁去徐府的时候,徐凤鸣明显从赵宁脸上看出了他极细微的变化。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可以伪装,但他的眼神是很难伪装的。徐凤鸣看他那样,就知道他今天心情不错。不过赵宁高兴是对的,尽管他跟赵瑾没有半点感情,但无论无如赵瑾都是他的叔父,现在这种时候能得到叔父的认同,于赵宁而言是非同一般的。连郑琰都察觉到了赵宁的好心情:“君上心情不错哈?”赵宁今天心情确实不错,再次看到郑琰那张脸他都觉得郑琰顺眼多了,还生平第一次好脾气地问郑琰:“你去哪?”“正好,君上来了我就不用再去找胡濯尘了。”郑琰倒是不把自己当外人:“我想请你帮我给殿下开点滋补养生的方子,他身子太弱了,我要给他补身体。”“他身子是那年留下来的病根,”赵宁说:“很不好补,你还是去找胡濯尘,他可能比我在行。”“行吧,”郑琰也知道赵宁不是专业的大夫,他这点医术还是徐凤鸣失踪那几年学的:“那我找他去。”他说完就走,徐凤鸣忙叫住他:“你现在去?”郑琰理所应当道:“不然呢?”徐凤鸣:“你没瞧见天黑了?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你就不能等天亮再去?”郑琰想想也是,现在都快二更天了,胡濯尘这会儿估计都睡了。于是走回来坐没坐相地躺在廊椅上,双手枕在头下,叹了口气开始自言自语:“都是我不好,我当初若是不气他,他也不会生病,现在也不会落下病根。”“你知道就好,”徐凤鸣说:“子敬为了你不知道受了多少罪。”郑琰没吭声,他侧头望向院落,今夜没有风,雪花纷纷扬扬,不断从黑洞一般的天上往下飘。徐凤鸣觑了郑琰一眼:“你可知道,你那年风寒,子敬给你熬了近两个月的汤药,那手上的伤就没好过。”郑琰倏然间从廊椅上坐了起来:“公子,你说什么?”“怎么,你不知道?”徐凤鸣扬了扬眉:“就连你受伤从大溪回来后,所有的药都是子敬亲自给你熬的。他每天守着那药罐子,每次都等药熬好了,再让侍女给你送过来的。”郑琰:“……”郑琰突然起身,要往回走,走廊尽头,姜冕披着斗篷提着盏灯笼来了。他手上那灯笼的光并不怎么明亮,仅能照亮他身周那一点地方,却跟屋檐上悬挂着的灯笼交相辉映,恰到好处地落在他身上。姜冕披着斗篷带着兜帽,面容在灯光下若隐若现,映着他原本就不凡的面容更为柔和。他从那影影绰绰的光里走来,衣袍随着他的步子轻微摆动着,犹如谪仙。郑琰当即迎上去,接过他手里的灯笼。“你们在聊什么?”姜冕走回来,放下兜帽,笑道。“没什么。”徐凤鸣瞥了一眼郑琰:“替你训狗呢。”姜冕怔了怔,忽然笑了起来:“凤鸣兄,你们别欺负他。”徐凤鸣:“怎么?心疼啦?”姜冕但笑不语,赵宁忽然说:“郑琰是个贱人,你不能太给他脸,否则他会蹬鼻子上脸的。”姜冕难得见赵宁开玩笑,望向赵宁,笑了起来:“赵兄今日心情不错啊。”赵宁不说话了,姜冕走到案几后坐下,郑琰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给他暖着。徐凤鸣给他们倒了杯茶,四人安静地坐在廊下听下雪的声音。徐凤鸣望向院外,忽然感慨道:“又是一年了。”“是啊,”姜冕说:“又是一年了。”徐凤鸣突然想起那年他们四人在赵宁暖阁喝酒的场景,时间飞逝,不知不觉过去了十几年。那记忆似乎很遥远,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徐凤鸣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记不清楚苏仪的样貌了。脑子里只隐隐约约,有一点大概的轮廓,却始终想不起来具体的面容。“这两天我看过各地呈上来的文书,”姜冕说:“今年各地的收成还不错,没有受多大影响。”徐凤鸣:“内忧外患,现在内忧已平,就剩外患了。”姜冕一听这话就明白徐凤鸣有想法了:“凤鸣兄和赵兄有想法了吗?”“我答应过姜兄,尽力帮他收复这破碎的山河。这是他的毕生夙愿,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试一试。”,!徐凤鸣眼神放空,似乎透过这漆黑孤寂、大雪纷飞的夜,看见了戴着面具,孤身一人站在缥缈峰上眺望凡尘的姜黎。他不言不语伫立在缥缈峰之巅,从春花灿烂到冬雪纷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山下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百姓担忧。可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如多年前的洛阳被围攻时一样,什么都做不了。徐凤鸣沉默良久,才重新开口:“子敬,你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该怎么办?先打哪国?”姜冕想了想,说:“卫国。”徐凤鸣跟赵宁对视一眼,显然,姜冕的回答跟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赵宁伸手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徐凤鸣则看向姜冕:“为什么?”“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姜冕顿了顿,似乎在思考接下来的话该怎么说,才能不让赵宁心里不舒服。赵宁明白姜冕在顾忌什么:“但说无妨。”“赵宁说得对,”徐凤鸣说:“子敬有话但说无妨,他不是听不得真话的人。”徐凤鸣跟赵宁这么说,姜冕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赵兄海涵。”“启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民心,”姜冕说:“启国自建国以来的名声就很不好。几十年前的平川之战杀降一事,更是将声望降到了最低。以后若是想在中原站稳脚跟,那么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卫国跟启国有平川之战的血仇……其实不单是卫国人,中原各国都对启国……说实话,百姓们对启国可以说是闻风丧胆。”姜冕说的没错,启国上边几位国君确实把启国的名声搞臭了。特别是三十多年前的平川之战,公孙止杀降这一行为,启国的声望可以说是臭名昭着。别说玉璧关外那四国的国君和公卿大夫们对启国是如何瞧不上眼,百姓更是闻风丧胆、谈之色变,就连徐凤鸣都看不惯启国的所做作为。赵家以武立国,被中原人称之为蛮夷之邦,多年来干的事也确实不怎么光彩。倘若赵宁不是启国人的话,徐凤鸣觉得自己宁愿选宋国都不会选启国。皆因他们的名声实在是声名狼藉,在整个神州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了。现在启国想笼络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卫国下手。若是这次能打下卫国,让卫国心甘情愿臣服,那么就做好了榜样,以后会顺利很多。姜冕:“再者,卫国跟启国接壤,根据远交近攻的策略,也应该先打启国。”郑琰听得直点头:“说得对,万一我们出去打仗,卫王那老东西带着人来端咱们老巢怎么办?”姜冕面上不动声色,手上轻轻捏了捏郑琰的手以示回应。郑琰乐开了花,脸都快笑烂了。姜冕:“当初卫国跟燕国,究竟是怎么绕进咱们边境这事还未曾下定论。若是真的从卫国边境借道西域过来的话,就危险了。最好的办法是打卫国,杜绝这种可能性。毕竟谁也不想在外面打仗的时候,再一次面临王都被围城的风险。”姜冕说着,眉头若有若无拧了起来:“可问题是……”“可问题是该怎么打。”赵宁说。徐凤鸣接着说:“打下来又该怎么管理,这一仗至关重要,又牵扯到平川之战的旧事,必须尽量将伤亡减到最小。”姜冕点头:“因为平川之战的缘故,卫国人或许会殊死反抗,若是真到了那一步,就得不偿失了。”“不是或许,”赵宁说:“是肯定。”这是必然的,几十年前平川之战,卫国人投降,结果公孙止转头就把降兵全杀了。再来一次,还是同样的国家,卫国肯定会殊死反抗。因为他们已经吃过一次亏了,知道投降是死,不投降也是死,那谁还会投降?可若是他们死不投降,到时启国大军一碾过去,人都死得差不多了,那就本末倒置了。不但笼络不了人心,恐怕会再一次激起联军抗启。但以现在的形势来看,又必须先打卫国。燕国地处西川,西川地势复杂、易守难攻,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作为屏障,根本不好打。楚国和宋国相邻,又依长江天险,而且还是离启国最远的。显然,在现在这种时候打楚国和宋国也是不明智的。谁敢保证燕国和卫国会不会再一次趁火打劫,出兵围攻大安城来端他们的老巢?还有就是到时一出兵,该怎么杜绝燕国出兵救援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跟燕国结盟。”姜冕说:“这世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四国看似关系好,各国之间往上数几代都有点娘舅关系,可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上的时候,什么关系都得靠边站。”,!这倒是真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有利可图,不怕燕国不同意。徐凤鸣笑了起来:“或许可以先写封信去西川,探探燕平的口风。”姜冕:“只要利益给到位了,他会同意的。”赵宁:“让林正阳去办。”“阿嚏!”院落间忽然刮进来一股寒风,姜冕受不住凉,这几天都有点受寒,这风一激,打起喷嚏来。郑琰心疼坏了,忙把兜帽给他戴上吵着要带着姜冕回去睡觉。徐凤鸣跟赵宁见时间也晚了,于是也回房了。徐凤鸣面露思忖,还在想姜冕今夜的话:“你觉得子敬的办法怎么样?”徐凤鸣跟姜冕都不是太:()戎马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