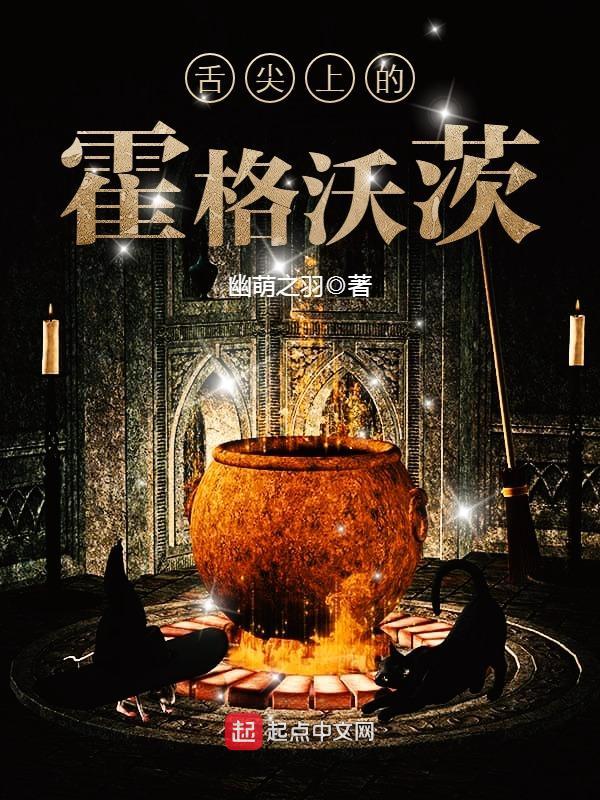奇书网>我们谈谈用英语怎么说 > 第149章(第1页)
第149章(第1页)
睫毛上还沾着水汽,时恪柔声道:“黎昀。”
小猫在清醒的时候总是满身防备,真醉了又毫无戒心,再难言的话都能轻而易举地说出来。
而恶劣的人性也总会挑在这种时候显现,当内心这处空缺被填满,就会出现下一个索求。
黎昀卑鄙的,有些想要趁人之危。他沉下声音,循循诱道:“我不是总出现吗。”
时恪轻摇头,“你最近只有在梦里才来。”
心间最软的部分被挠了一下,又疼又痒的,黎昀反被拿捏,后悔起这几天怎么能忍得住不给一点消息。
他放慢呼吸,“你每天都会梦见我吗。”
时恪懒懒的从鼻子里“嗯”了一声,酒精的灼热仍蒸腾着身体,昏沉到喋喋自语,“对不起……我把你赶走了。”
黎昀问:“那为什么要赶我?”
“因为害怕。”
“怕什么?”
时恪像是顿了一下,轻哑道:“怕你……觉得我恶心。”
黎昀皱起眉,“为什么?”
车内忽然陷入沉寂,好半晌,时恪才摇了摇头,“说不清楚,心里不舒服。”
记忆碎片在脑海中如雨珠坠下,从一句“要帮忙吗”,到彻夜陪伴在画室寻找证据的身影。
黎昀从不怀疑他的过去,总是毫不犹豫地出现在身边,甚至不曾因林轶而退让,也不曾因伤疤而远离。
这样好的人,被他赶走,这样温暖的人,不属于他。
而最难堪的,是自己的喜欢无处躲藏也无处安放。
时恪似是穿透雨幕,在氤氲中望向黎昀的眼睛,“我的画不见了,你也不见了。”
那副画是个秘密,内容只有时恪和他两个人知道,与原图相比,多出来的那只飞鸟,究竟是什么含义?
想要知道答案的心过于迫切,黎昀的手深陷进软皮座椅,索性换了个问法,“那为什么要画那幅画?”
时恪:“因为喜欢。”
一些关键词听在耳朵里,总是让人起应激反应。
黎昀眉心微跳,忽然有些不敢呼吸,按捺住心绪,用温柔而低沉声音继续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