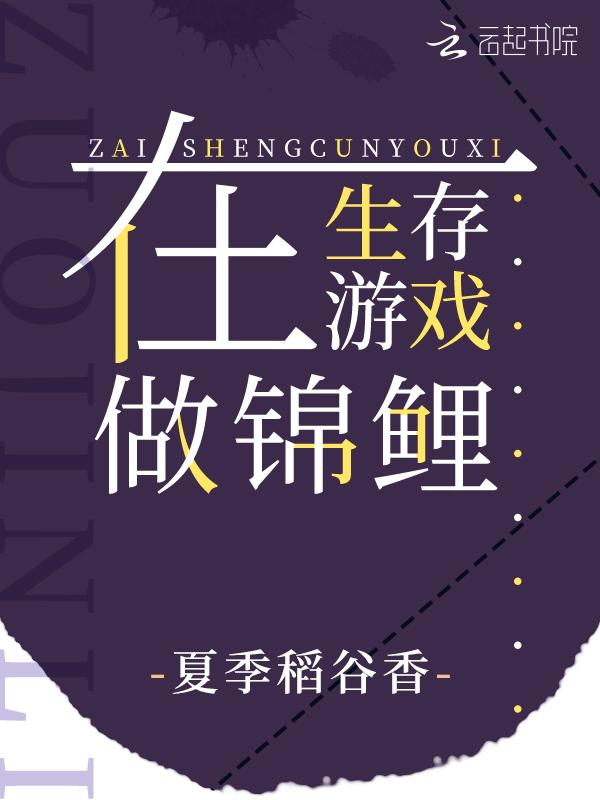奇书网>人类契约灰橙txt > 第1033章(第1页)
第1033章(第1页)
“我妈妈在家,还有一个哥哥,他大概出门了。”阿硫费劲地搬开沉重的石门,示意几个人一个个弯腰钻进低矮的洞窟。
一进入门内,诺里就闻到了淡淡的味道,非常诡异,比较难闻,但不是臭味,而是种……难以形容的刺鼻味道。过了狭窄处一抬头,她就明白了味道的出处:
墙边一排支架,挂着白白的柔韧的筋,好像细长柔润的藤萝植物,在轻轻摇曳。支架旁一个小铁盒里,装满了半盒的各式指甲,有纤小的也有粗糙的,大致都保持完整的形状。
一个老妇人,穿着件不合身的睡裙,坐在一架类似纺车的工具前,她的膝盖上横摆着几丛干枯长发,正在被她变形的手指编织起来。她听到了声音,有气无力地唤一声:“阿硫是你回来了吗?”然后侧过头,看见了诺里等人,当时露出了十分渴望的眼光。
诺里这辈子第一次,被人用这种……极端饥渴的眼光打量,目光火热,却让她感觉冰凉,仿佛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团脂肪丰富的叉烧。即便诺里已经见遍了风浪,很难有什么东西能惊吓到她了,但是此刻,她要努力控制自己,才能不当场吐出来。
婓尔卓稍微用力地抓住她的手,用行动暗示她不要离开自己附近。诺里偏过头低声和他说:“我从来没想过,人到底能堕落到哪种程度。这些……真的惊到我了。”
“妈妈!”阿硫挤过来,挡在一行人前面,“他们是神明大人的侍从,他们要代表神明大人来拯救我们了!”
艾芙夫人只有40几岁,但和40多岁的贝尔夫人,还有萨芬夫人相比,简直宛若两代人。她的额头爬满了皱痕,眼尾深深下垂,整张脸写满了苦难。现在,所有苦难的表现都被欲望挤占了,她不能自已地盯着诺里流口水,甚至思维散漫,无法集中。
阿硫左右张望着,一边问:“哥哥在吗?我们得给神明大人的侍从们带路,去一趟圣巢。”
“你要去哪里?”另一个更年长些的青年从另一间洞穴出来,他跟阿硫蛮像的,瘦高细长,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衣服松垮垮挂在身上。皮肤很苍白,是一种偏向青绿色的苍白。他原本应该比较清秀,但是长期环境的荼毒,让他头顶的棕发稀疏,露出一块头皮,牙床萎缩,齿根晃动,活脱脱未老先衰的样子。
“圣巢有点难走,我只是远远看到过,没有真的走去,有点认不得路了。”阿硫朝着婓尔卓解释,“我哥哥去过,他曾经进入到圣巢里面。不过他没有惊扰神明大人!他只是误入,且那时神明大人不在巢里。”
“你叫什么?”婓尔卓看了看兄弟两个,去问那个兄长。
他一个字也不愿多说,简介地回答:“阿氢。”
看到一群人马上要离开了,艾芙夫人激动得原地打转,就像看到食物自己长腿跑了。诺里赶紧打开背包,“我有一些营养剂,都给你了,只要你别再用看食物的眼光看我了。”
艾芙夫人奇怪地看着她手里的注射器,无法把这些针筒和食物联系起来。诺里只能放在石桌上,最后干巴巴安慰她:“再坚持一下,马上一切就会好转的。”
阿氢带上一盏废旧的灯,挑在一根长杆上,在浓雾里散发着昏黄微茫的光。诺里看了一眼,忍不住问:“我猜猜,这里面烧的是脂肪吗?”
阿氢瞟了她一眼,跟兄弟不同,他的态度十分冷漠,一点不见仰慕或者崇拜。“你有意见吗?”
“我没有意见,我就是好奇……你们没有邻居,是因为邻居都变成早餐晚餐,还有挂毯提灯了吗?”
阿硫替兄长回答:“我们没有早餐,每天只有一顿晚餐。因为晚上不吃东西实在太难睡着了。”
“……”诺里沉默下来,实在不知道应该表达自己的同情还是厌恶。
前面的路愈发难走了,碎石滩的尽头是一汪浓绿色的酸池,咕嘟嘟冒着泡泡。阿硫和阿氢两个人不由分说卷起裤腿,好像准备淌过去。
婓尔卓蹲低下来,示意诺里爬到他背上。灰鳍在旁边看着,不满地说:“有人为我们两个伤员考虑吗?”
诺里挥挥手,“要不然你们两个在这等着吧。”
“不要。”琪拉尔马上拒绝了,“万一里面出现变故,我们在外面都不知情,那是等还是不等?我一定要一起进去!”
灰鳍啧了一声,自认倒霉,“算了算了,你上来吧。我多少比你皮糙肉厚些。”
诺里忽然想起来什么,“我可以让编织者衔着你们过去。”
灰鳍抬头看看天上的巨型金属飞蛾,连连摇头,“要是扎穿我怎么办?我宁愿游过去。”
“或者……我可以切断你的痛感。”
“什么?”灰鳍震惊了,“怎么做到的?你怎么能切断我的神经感知呢?”
“原理很难解释,反正你只要知道,这是我最新学到的小技巧就行了。”
灰鳍马上驼上琪拉尔,灵活地扑腾进酸池里,“你只要离我远点就谢天谢地了!我不想让你在我身上做实验。”
但是皮肤一接触到酸性液体,灰鳍马上就失去了灵活性,他被刺痛了,站在原地忍受了一下,才慢吞吞艰难地继续行走。身后阿硫和阿氢也陆续进入液体,他们的忍受能力明显强很多,只是咬着牙一声不吭,慢慢地行走。
婓尔卓是最轻松的那个,虽然酸液对他的组件也有腐蚀作用,但他不痛不痒。“这大概是变成生化人以来,最幸运的时刻了。”
诺里在他背上,“是,当生化人也是有很多便利,但是你可别当上瘾了,终究还是要当人的。”